城市上空的雞鳴 八條漢子和二個女兵_頁2
,畢竟在這種特珠的情況下,有些事情是不能按正常的規律去要求的。
是的,這篇小說最成功之處就是在特珠的環境下把這八個和兩個的關係處理得相當合情合理。令人動容。)
夜,漫長而又難奈。我們八個男兵如同在進行一場接力,與生命賽跑的接力。而處於深度昏迷的女兵就是我們手中的接力棒。
可她們畢竟是有血有肉的女人啊!在這與世隔絕「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六月穿皮襖,四季雪花飄;頓頓夾生飯,氧氣吃不飽」被稱為「生命禁區」的地方,我緊緊地摟抱着幾近**的女兵,漸漸地,猶如冰人的女兵身體開始有了點熱氣,並在我懷中輕顫了一下,一絲兒女性身上特有的好聞氣息鑽入鼻孔,我莫名其妙地一陣顫慄,女人!我摟抱着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我的臉像火炭一樣燃燒起來。
班長遽然睜大惶悚的眼睛,臉色「唰」地變得血紅,他威嚴地乾咳了一聲,並恨恨地在我的屁股上狠擰了一把,灼痛使我一下子驚跳起來。
班長甩下大衣,迅速地走向槍架,抓起一支衝鋒鎗,「嘩」地壓上了彈匣,然後,把其它武器全部鎖進了槍櫃。班長提着槍,一雙血紅的眼睛猶如雷達掃描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掃視了一遍,便沖沖地向風吼雪舞的門外踏去。戰友們愣神須臾,緊接着便心領神會地相跟着走了出去。
哨卡外風雪正緊,核桃般雪團驚恐地撲過來卷過去左衝右突。我們面向班長牢牢地站定,迷離的眼睛裏寫滿了惶恐。報數完畢,只見班長竭力地挺直腰杆,「咔」地將衝鋒鎗子彈推上了膛,朝着迎面撲來的風雪吼道:「誰他*的想胡來,老子一槍崩了他!」僅此一句,便撇下目瞪口呆的七條漢子徑直回屋。
接力還在繼續,生命與死神還在賽跑。
(這是生與死的一場接力。八個士兵輪流着用自己的熱氣來換回女兵的體溫。這也是人性與動物性的一次交量。這個接力的結果是男兵把女兵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這個人性和動物性的交量過程中,人性戰勝了動物性。
看了四遍,這四遍都在這裏我差點流出淚來。我深深地為生命的力量而感動,又深深地為這些士兵強悍的人格而讚嘆。這篇小說在我心裏就有了迴腸盪氣的感慨,極富藝術感染力。這是一曲生命和人性的讚歌。)
兩位女兵終於相繼甦醒了。當看清擁抱她們的是同樣赤胸露懷凍得嗦嗦發抖的陌生男兵時,一個個滿臉羞澀,雙眼湧出了激動的淚花。確定兩個女兵安然無恙後,班長迅速示意我們離開套間,並隨手「叭」地帶上了角門,「嚓」地扯下鮮紅的銅號裹布,將套間的門把和門框牢牢地綁在了一起。
(女兵被活過來了,生命從死亡那兒跨過去了,但人性和動物性的較量還在繼續着,這些可愛的男兵用笨拙的方式戰勝了自己。)
昏暗的燭光抗議地跳了兩跳,班長威嚴地席地而坐在套間門口的一條毛毯上,臉前放着我們共有的半斤多莫合煙,和一沓裁好備用的報紙條。班長猛抽了一口自卷的喇叭煙,冷峻的絲毫沒有商量餘地的命令便裹挾着團團煙霧從口中噴出:「大家統統睡覺,今晚有我值班。」
如此不尋常的夜晚,班長一人值班,七條漢子都有點不放心。哨卡里生活太枯燥了,十個月的封山期阻隔了與外界的聯繫,這裏海拔太高,收音機沒聲,電視機沒影,幾乎成了年報的日報,一旦上山,戰友們都瘋了似的去搶去讀,日復一日竟能將上面所有的文章一字不漏地背下來……
時間離拂曉大約還有兩、三個鐘頭,狂虐的低低嗚咽的暴風雪終於精疲力竭只剩下喁喁絮語在纏綿。有戰友在不住地翻身。班長仍舊威嚴地抱着槍悠悠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莫合煙,雙眼機警地來回逡巡。
天色微明,戰友們一個個醒來,發現報務員正鄭重地向握槍席地而坐、身旁扔滿煙屍的班長匯報:「軍區來電,救援的飛機中午就到……」雙眼佈滿血絲兒的班長輕舒了一口長氣,神情倦怠地關閉了衝鋒鎗保險……
(人性和動物性的這場交量是另一場暴風雪,終於這場暴風雪跟所有的暴風雪一樣過去了。)
八位男兵和兩個女兵索然寡味地吃着一年四季天天如此早已吃膩了的大米飯和紅燒豬肉、牛肉罐頭。用過早餐,戰友們圍着爐火默默地坐着。不知是為了打破這令人難堪和
-
完本感言(下) 真不知道,免費章節居然不能點讚,那麼算了,強迫症時間到,就當點夠一百個贊了,繼續碼字嘮叨。 說起沒斷更,有傳言說官仙曾經斷更過,因為地震啥的。 各
-
終章 冥君去世一年半後的冬天,司徒百合臨盆。Ww w. Q Β5 。c oM// 那天的風雪下得兇猛,足足兩天兩夜不停歇,馬車無法在厚雪堆里行駛,街道封閉,產婆被困在半路上,最
-
寫完這本後寫篇小甜文《你總是暗戀我》,求戳進專欄里收藏嗷嗷嗷! 夏之衍招惹了一個神經病,這個人想替他洗澡,替他刷牙擦臉。做這一切的時候,眼睛還亮得嚇人,嘴角甚至微微翹起,還蜜汁臉紅(?
-
1號家庭,辣媽岳母蘇麗娟,外表靚麗,內心時尚,早年喪父,一個人拉扯着孩子,但為人豁達樂觀獨立,一心想要女兒嫁給金髮碧眼的洋女婿,沒想到女兒卻嫁給了日本人。與女婿上條京介生活同一屋檐下的蘇麗娟,
-
簡介: [預收文《和前男友哥哥協議戀愛了》,求個收藏鴨。] ++++連續失眠三個月的路星眠在網上下了一個哄睡的單子。+ 不抱希望的他在聽見對方的聲音之後,第一次就有了想睡
-
「怎麼會這樣?身體……」「屍體……」「怎麼,我還用咒力嗎?」秦乞的周圍是黑茫茫的一片,昏黃不見天日,唯一的亮光,只有雙手上的符咒,但是咒力卻……
-
重生在哈利波特的故事裡,身份卻是黑魔王的女兒!為了能平安的度過一生,她不得不努力掩飾身份。她的話真真假假,又有誰能分得清······
-
從鄰居的美艷少婦,到小賣店的新婚不久的嫩菊小媳婦,到班花朱娜,婦女主任,美女大學生村官,村長女兒,鄉長夫人……一步步向上般,走了一道美女的階梯,攀岩着更高聳的..
-
微信群裡面發現有一個小視頻裡面的女主像極了妻子,她最近變得很奇怪,夜晚下班很晚才回家,穿出去的絲襪沒有穿回家……
-
暫時無小說簡介


![天下第一少女攻[重生]](/files/article/image/156/156916/156916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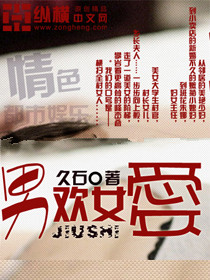

![[快穿]小受總是在死](/files/article/image/34/34871/34871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