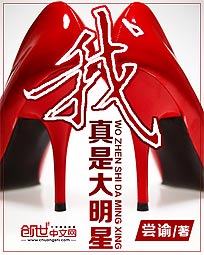白夜浮生錄 第四百二十九回:迴路漫漫_頁2
哪兒都是活。
彌音從不會像那些富貴人家一樣,更不像那些視其為搖錢樹的人。於她而言,阿淼不論是什麼花色什麼模樣,都是她絕無僅有的寶物。
也是她的朋友。
它是自己唯一的朋友嗎?也許不是,她還是認識一些人一些,傻傻的人。他們,或者至少他們中的一位姑娘,也曾稱自己為友人。可不論真假,那也只是單方面的罷了,自己似乎從未真正這樣認可過——如今看來,她也覺着自己實在不配了。
這般前後的心情是如此不同而轉折從何處開始?她也不知該問誰去。
它是自己最初的朋友嗎?也不是。第一個朋友,應當是那個她連姓都不知道的女孩。阿淼的名字,便是她名字的影子。但那個女孩從何時起,不再能被稱為「朋友」,關於這個時間節點,她大約還是能憶起的。可她沒法兒深入去想了,似乎沒多思考一陣,就是對過去愚蠢的自己狠狠的一巴掌,就是對霜月君正確判斷的褻瀆。
但它定是自己最後的朋友了。
不論什麼時候,都不曾有人對她說過這樣的話。
我多希望你能獲得幸福。
很多人看在霜月君的情面上照顧她,霜月君也是希望她能好好活,活得好。那個少年,那個贈予自己琴弦撥片的少年,也說希望她多笑一笑。可那又當如何?什麼才算作活得好,卻沒人告訴她;她究竟想不想笑,也沒人問過她。似乎所有人在意的,都只是她表現出來的模樣。只要看上去夠好,夠快樂,便不會過問,不會追究。彌音向來是直來直去的人,不喜歡無謂的表演,也從不強迫自己做不喜歡的事。她倒也知道,那些人倒沒什麼壞心眼,也是真心盼她能別整天悶悶不樂的。但說實在的,對於這些,她一概無法感知。
唯獨阿淼,一隻毛茸茸的貓妖,能對她說出這般話來。更重要的是,不是靠「說的」而是最直觀的「傳達」,真心實意地「感染」。
酸澀,又甘甜。
原來我是想要幸福啊。
「我不知道,」她哽咽着說,「我不知幸福為何物。我也從未奢求過這種東西。它、它聽起來很好看——但我看不到,我也抓不着。我只知道有你相伴時,我是能挺過很多事的——過去,到我拋下你為止。我以為我缺爹娘愛我,缺朋友照顧我,我以為我想要關注,想要錢,想要力量,想要快樂我以為了很多,卻都是虛的,看不見摸不着的。就算它們落到我手裏,我也拼命去抓,卻什麼都沒抓住」
原來我是想要幸福啊!
「我再也得不到了!」她聲嘶力竭地哭訴着,「我還該做些什麼的!我走到今天算不得是無辜,但我也不會認罪。一切好的壞的,都是我該。但我還是我還能做些什麼,為你做些什麼的!如今你告訴我了我卻從未問過你想要什麼。我已然淪為妖物,你也如此,我該能為我的——我的朋友,做些什麼的。」
「」
阿淼臥在那兒,一動不動,像個娃娃。但它直勾勾盯着她的那雙眼睛,在火光之下,分明是如此靈動。
「是了。」安靜許久的腦海再度出現聲音,「阿淼也有自己想實現的願望。彌音你能幫我嗎?」
「你想做什麼?」彌音直起身子,「我什麼都可以幫你!」
「其實」
「其實?」
其實——
其實,倘若,倘若說。
在停止呼吸的那一刻,阿淼就不該再活呢?
阿淼一直以來的願望,其實是想平靜地、安靜地轉生呢?
沒有世俗的紛爭,沒有紅塵的牽絆,帶着一份生前不輕不重的思念,投身輪迴的洪流中去。在得知這般意圖的一剎那,強烈的眩暈感幾乎要劈開彌音的頭顱。
是自己的一廂情願終究害了它,讓它在凡間蒙塵,讓它的自由被剝奪,讓它憑白承受本不該承受的是非善惡、黑白抉擇。
時至今日,綺語的惡使才完全意識到,曾身為人類之時的自己有多麼自私。她本是很清楚的,清楚自己對任何人都那樣刻薄。可她一向以對動物友善而自居,卻從未問過這個小動物的意見。她和最開始一樣,只是自顧自地,將自己的意願默認為對方的罷了。
長久以來的堅持全部都是任性而已。
-
防火防盜防閨蜜,老婆太聽閨蜜的話,說啥信啥。 梁燦文原本和和睦睦的小家庭,因為老婆太聽閨蜜的話,最終離...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離婚後才發現我被覬覦很久了》還不錯的話請不要
-
愛藍天,愛綠樹,更愛波瀾浩瀚的大海。 淺海魚,深海魚,龍蝦還有大海蟹,吃貨的世界怎麼能少了海鮮? 快艇,遊艇,海釣艇,還有巡航艇,其實豪華遊輪才是王道。 家裡養着棕熊、白熊和浣熊,漁場還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簡介: 任你權勢滔天,任你富可敵國,在我面前不要囂張。我是葉秋,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小說別名:蓋世神醫。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邪神祭副本完結可宰白柳在失業後被捲入一個無法停止的直播遊戲中,遊戲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怪物和蘊含殺意的玩家一開始所有人都以為白柳只是個誤入遊戲的普通人後來,他們才明白,是這個遊戲用勝利和桂冕在恭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為了成仙,姜辰決定積累功德。 民以食為天! 姜辰就從吃的方面着手,以雜交技術培育出優質的糧種,讓糧食產量暴漲,使得世間再無饑荒,再無人餓死。 世間沒有公道,天地沒有善惡,強者
-
一心想當明星的張燁穿越到了一個類似地球的新世界。電視台。主持人招聘現場。一個聲音高聲朗誦:「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着烏雲。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暴風雨,暴風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