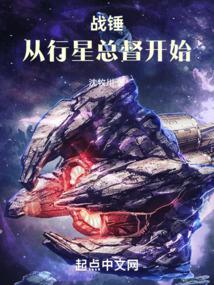南明風雨之血沃中華 9節伊人生死
現在,這個時候還不是說岳效飛此人如何做時候,姑且讓我們將這個老是霸佔着舞台的傢伙扔在一邊,並且將時光朝前推進一年,為大家解除一個小小的疑惑。
傍晩,海波在夕陽下泛着魚鱗一般的光點,一台被神州城的船員們戲稱為「水棺材」的淡水製取設備,飄浮在海中。
大的方盒子之上,橫臥着一個身穿神州軍護甲的人,脖子後面露出的長髮說明她是個女性,她正是慕容楚楚。
這就是那個岳效飛在江南首次以這個世界上出現的「蛙跳作戰」大勝,而又充滿無奈傷心感情的歸途。當然他不知道,因為這樣他正正經經地進行了一次,行為頗為高尚的民族大融合。
遠處來了一艘不大的船,掛着中國式的硬帆。只是它從何處來,要到何處去只怕沒人知道。
很快隨着天色越來越暗,漸漸已經幾乎要看不清海面的時候。這艘船距離那個水棺材也越來越近,這時小船之上已經伸出一枝竹稿挑着一盞孔明燈,照亮了附近的海水。
「爹爹……爹爹……海里漂着個物事呢,看不清楚……」
隨着一個青年的聲音,船上的艙門一開,一個年約四旬的中年書生打扮的人,邁步走了出來。
他是山東琴島(今青島)嶗山腳下人士,人稱琴島針王的欒易之(字慶生),因為清軍入關之後,不斷欺凌中華百姓,欒易之不願忍受剃髮易服之恥。
遂變賣家產,千方百計購買海船一艘,闔家前往南洋一帶尋找,那蓬萊仙島般的沒有苦楚的去處。
一路之上,欒易之時常生出對於故土難離的嘆息。然而,他又不能親眼看着自己家人遭受滿人的欺凌,或者剃髮易服之舉。
如此,去與不去兩種情懷交織於心裏,所以整天也不見露面,僅只躲在艙里借酒澆愁,殊不知借酒澆愁愁更愁,便得他更難得偶爾出來看一下海上風光。
此刻聽到自己孩兒欒平字躍之的招呼,卻也只好自艙中出來,希望目睹「海上奇景」或可解愁懷也說不定呢!
這時的天,已經幾乎黑透了,僅憑着孔明燈那微弱的燈光,實在看不見什麼。好在這天夜裏僅僅只有微微小風,倒沒什麼風浪,如是仔細觀察倒也並非雙眼不能視物。
欒易之用手遮了眼前孔明燈和桅頂燈籠的光亮,運極目力努力看去,卻被他正正的看了個清楚。
「卻似個怪模怪樣的箱子,那上面趴着的只怕是個人吧!快……快……快叫人來!」
隨着他的一聲招呼,船上的家人還有幾個水手都跑了出來,一起向他指的地方望去。接着船老大轉了舵,海船向那個方向緩緩航去。
欒平也跟着水手們一起忙碌着,終於海中的人被撈了起來。
「呀,好像是個姑娘呢!」
欒易之聽到了兒子的招呼,伸手在撈上來的人鼻前探了探鼻息,再拽起她的手臂來,診了下脈,立即斷定這位姑娘受創甚重,又在冰冷海水之中泡了相當長的時候,只怕時刻都有香消玉磒的可能呢!
一邊為她診着脈,邊伸手探懷掏出他須彌不離身的針包,嘴裏急道:「平兒快叫起你娘來,另外要廚子燒些熱水來,煮起薑湯,還要以下幾味藥材……」
隨着他一疊聲的招呼,船上的人忙碌了起來,水手們這裏甚至也把那個「水棺材」撈了起來,只是苦於沒有人認識是什麼東西罷了……。
隨着時間的推移,天色漸漸亮了起來,忙碌了一晚的人們終於可以透一口氣了。這時才睡醒的欒平洗漱以畢,來到了忙了一晚的父親面前。
他才一進門,卻又立即的小心的放輕了腳步,因為她的母親大人因為一夜的勞頓,此刻伏在床邊睡得正香,而父親卻倚在一旁的小几之上頭一點一點的打着瞌睡。
「也是,昨夜裏救了她,可連累的爹娘個個都無法安睡,只可惜自己是個男子卻幫不上母親半點忙。」
一面想着,小心翼翼的邁動步子走向艙室的深處,昨天夜裏只就着燈光掃了一眼,只覺得那姑娘的容顏也有幾分秀麗,只是不知眼下傷勢如何。
哪知,他這才一邁步,卻一腳踢到了一旁立起靠在小几上的木盆,倒下的木盆倒發出了好一陣的響聲。嚇得他只吐了吐舌頭,忙收了腳向後縮去。
就算他收腳在快,也已經驚醒了在几旁打盹的父親欒易之。
-
簡介: 她穿成書里的炮灰,最後被…… (簡短小故事) (甜文篇) 1、炮灰侯夫人(完結) 2、女主繼母(完結) 3、炮灰表小姐(完結) 4、炮灰淑妃(完結) 5、炮灰白月光(完結)
-
簡介: 壞消息是死了。好消息是穿越了。壞消息是穿的詭秘。好消息是沒看過書。 壞消息是……你剛剛誤吞的,好像是一份幸運兒的非凡特性。-------- 「作家需要講究邏輯,但
-
簡介: 這是一場2K時代的靈魂與戰錘30K時代的碰撞。當零號原體擁有穩定的靈魂,炙熱的亞空間本質能否燒灼一切。 帝國能否在大遠征時衝破四神的陰謀,原體們能否摒棄幻想站在一起。
-
簡介: 玄幻世界,實力為尊。有實力,你就擁有一切,你可以不講道理,不講道德仁義,甚至連基本的人權都可以不講。 ……既然這樣,那就別怪我不吃牛肉了!
-
簡介: 【斷案為主】【劇情流】【江湖廟堂】【同級無敵】【偏傳統】 穿越到高武大明的許山,成為了一名錦衣衛校尉。 獲得『通靈還願』系統,覺醒神通——通靈! 只要能替死者還願,就
-
簡介: 問與答環節: Q:別夏xi,為什麼當初會選擇和權至龍在一起呢?r/> A:當然是因為他有錢啊(理所當然) 權至龍在旁默默吐血,又安慰自己,沒關係的,好
-
簡介: 五年前,葉家被滅,廢物葉辰神秘失蹤。五年後,那個葉家廢物回來了! 帶着一身通天地泣鬼神的修為回來了!這一次,葉辰要讓蒼天敬畏!要讓大地顫抖! 要執掌一切,登臨蒼穹
-
簡介: 【戰錘+種田+太空歌劇】第41個千年,暗黑肆虐!人類帝國失去了一半的疆域。> 上百萬顆星球遭受到混沌的侵襲!饑荒遍地、犯罪肆虐、邪教叢生……位於帝國暗面的厄斯星正
-
簡介: 穿越成了蜀王李恪,剛睜眼,就被太子陷害,和李靖女兒睡在一起。 李靖告狀,李世民準備活活打死李恪餵狗。 就在眾人準備吃瓜時。 李恪激活了最強背景解鎖系統,系統發布任務:
-
簡介: 衛淵本無大志,但在時代洪流中不得不走上征戰四方、開疆闢土之路,直至關山踏盡,未曾白頭。/> 不正經的簡介一:仙人也怕工業化!這是一個發生在玄幻世界的工業革命的故事





![[娛樂圈]吸金男友](/files/article/image/335/335902/335902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