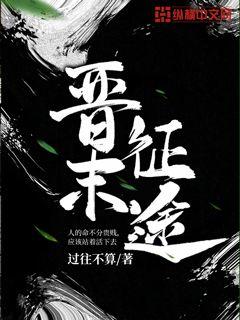瓜田蜜事 7.第 7 章
郭嘉緩緩攤開手,掌中一把蒙着綠胎衣的白南瓜子兒,沒有一絲缺損,圓鼓鼓肥胖胖的。輕輕拈了一枚在夏晚手中,柔聲道:「今兒多謝夏晚姑娘。」
夏晚看到的郭嘉,身上只穿着件中單,一頭黑髮當是新洗過,半干,柔柔披散於肩。
天然去雕飾,清水出芙蓉。
夏晚腦子裏忽而想起這麼句話來,那是私塾的於夫子在床上形容自家小妾的,她怎麼覺得用來形容面前的男人,也格外合適呢。
他眉鋒輕簇,那兩隻眸子仿如幽深的寒潭,清澈且冰冷。
只望着他於明滅的火光下如冷玉般的一張臉,夏晚微含羞的掃了他一眼,暖燈明滅,燈下笑的人比花嬌:「夫妻之間,說什麼謝不謝的。」
分明,方才他還好好兒的,夏晚這句話一出,郭嘉隨即就變了臉色。
「走,我送你回去。」薄唇一掀,他冷冷吐了幾個字出來。
夏晚正在猜這人為什麼忽而變臉,便聽郭嘉又疾聲說道:「你是個好姑娘,當初在蚩尤祠就差點死過一回,既能保得一條命,就該嫁個好男人,我還不知能活到那一日,你嫁給我不過糟踏自己。」
夏晚抿着唇,兩隻微深的眸子裏迅速的積蓄着淚水,悶了半天,小聲道:「我不怕做寡婦的,我潑辣着呢,便做了寡婦,也不會受人欺負,更不會主動去亂勾搭人,讓你死了也叫人戳脊梁骨兒。」
在鎮子上跑了近十年,她就沒叫人欺負過,也只是在他面前才低聲下氣而已。
郭嘉着:「可我若是死,就不想在世上再留個未亡人。」斬釘截鐵的,他伸手一拉:「嫁妝已經捆好了,走,我送你回紅山坳。」
夏晚一隻細腕叫他扯着,從白底紅花子的窄袖兒里生生露出一截來,整個人叫郭嘉從椅子上扯了出來,眼看就要撞上他的胸膛,兩隻手拳在一處,也不說話,一幅楚楚可憐的樣子,眩然欲泣,就那麼凝目望着他。
郭嘉再一拉,她那噙了滿眶子的眼淚骨碌碌就滾了下來。
兩隻微深如清水的亮眸兒,淚水也格外的足,大約也是太難堪,又忙不迭兒的擦着。
慌不擇言,她緩緩揚起一隻手來,又道:「我真會好好替你守寡的,咱們水鄉鎮還沒有貞潔牌坊,等你死了,我從朝廷給你掙座貞潔牌坊回來。」
一隻手比劃着,她道:「就那種,刻着咱倆的名字,叫後世人永遠永遠都能銘記郭嘉和夏晚的那種。」
說着,夏晚仔細看對面男人的臉,他眼裏無悲無喜,薄而鋒利的唇角就那麼微微的抽着。
「走!」他又是輕輕一拉,微微的不耐煩。
夏晚也急了,忽而一個強掙,一把就甩開了郭嘉的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既嫁進來了,就沒有走的理兒,更何況,我都想好替你守寡了,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郭嘉好歹也是個秀才,人,不好跟這小姑娘動粗,低聲道:「我不需要人替我守寡,快快兒的,我背你回紅山坳去,叫你爹替你再找個好人家。」
夏晚一直往後退着,怎麼看這人眼中也是一丁點的憐惜也沒有,心說軟的不成來硬的,我既嫁過來,你就趕不走我。
她兩隻眸子晶晶亮着,忽而柳眉一豎,立刻就成了個兇相:「我知道你為甚不肯娶我,你喜歡田滿福家的小寡婦水紅兒,你非是不肯要我替你守寡,你是怕你娶了我,水紅兒要另嫁他人。」
田滿福是對門田興旺的二兒子,死的早,留下個二十四五歲的寡婦,名叫水紅兒,生了一張極為勾人的臉,也是人如其名的風騷妖艷,在這鎮子上算是花名在外了。
田興旺身為田氏一族的族長,平日裏行的端坐的正的,想趕那水紅兒再嫁吧,她抱着兒子就要尋死,放在家裏吧,她整日哭鬼一樣嚎個不停。
幾年來,把個田興旺氣到幾番吐血,拿起棍子欲要抽她一頓吧,她把個遺腹子墊在屁股上,抽也抽不得。
因是對門對戶,常常三更半夜的,對門就能清清亮亮傳來水紅兒打兒子田狗剩,狗剩嚎啕大哭的聲音。
用郭千斤的話說,就是小寡婦夜裏沒男人睡不着,發了春無藥可解,又在打兒子煞春勁兒了。
郭嘉原本憋了滿滿的寒意與冷意,想把小夏晚給嚇走,叫她這麼
7.第 7 章
-
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 且看秦尋在這亂世之中,如何爭奪江山坐擁美人,博一個青史留名! -------------------------------------
-
一個偏僻的農村,一段糾結了近一個世紀戀情;一群夢寐以求獲得土地的農民......女主人翁為獲得土地,保護土地,經營土地而經歷的人生滄桑,親身經歷了靠土地磨生的農民從苛政猛如虎舊社會到種田拿補貼
-
還記得當年那個白馬銀槍的少年郎 那北平火車站的一瞥 那個羞澀的姑娘 那些吃過的屈 那些受過的傷 那些拜過的兄弟 那些說好的理想 那些快意恩仇的江湖,那些
-
時間:某一天。 地點:東京都米花市豆垣本家(原米花神社駐地)。 人物:豆垣淳、毛利蘭、工藤新一、毛利小五郎夫婦、工藤優作夫婦、鈴木園子及其家人等。 起因:毛利小姐
-
這個世界,有儒;有道;有佛;有妖;有術士。 警校畢業的許七安幽幽醒來,發現自己身處牢獄之中,三日後流放邊陲..... 他起初的目的只是自保,順便在這個沒有人權的社會裡當個富家翁悠閒度日。
-
【【2017這個歷史照樣靠譜徵文】參賽作品】穿越到梁山泊沒來之前的扈成有三個緊急要務:第一:給妹妹找個好對象,低於一米八五不要。第二:給自己找個好老婆,不是白富美不行。第三:給家裡找幾個好保鏢
-
一個宅男得到系統然後重生到明朝末年的太子,然後輔助父親讓大明崛起,當然那個世界是不同的,裡面的世界將是現在地球的十倍,是作者自己想象的,當然也有模仿,希望大家支持我,希望大家來支持,變書玻璃不
-
當李一醒過來的時候,他竟然莫名其妙的來到了大秦國,這也就罷了,畢竟這年頭,誰還不能穿越了,最關鍵的是系統呢?我他麼的這是個什麼狗屁系統?…… 孟大姐,你能不能別哭了,我這好不容易修好的…
-
快穿之絕頂攻略無彈窗的簡介: 原名《快穿之掰彎你跑》這是一個總是到關鍵時刻,就穿越,掰彎就跑甜(暗)蜜(黑)幸(不)福(虐)最後在一起的悲催故事。從來沒看過快穿文的伍偲羽,心血來潮的打
-
“半城黃沙埋忠骨,一縷狼煙寄悲情。”活着便會不易,活在一個烽火連天的時代更是難上加難。既然來到了這個世界,那就只能好好地活下去。他並不想為萬世開太平,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