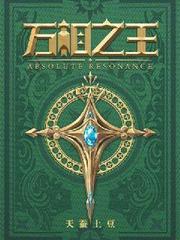我在東京當文豪 019 你管這個東西叫做隨便寫寫?
回到家裏,大島和也水都顧不上喝,直接將手稿拿出來,裝訂好,準備閱讀。
在進入家門之前,他特地在外面吹了一會風,為的就是醒醒酒,好讓自己的腦子利索一點。
之前北島駒只是用了寥寥幾句,將一眾編輯撥撩的不上不下,這下可好,整本都在這裏,一下子就仿佛是渾身被塞滿了一般,無比的充足。
這一次北島駒在開篇上寫了一個梗概。
來了來了,又是熟悉的味道。
大島和也泛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他就是這幾句話給撥撩的不上不下,這幾日根本就是滿腦子都想着那些情節。
北島駒那個字跡依舊很好看。
故事由駛往雪國的列車開始,窗外不停掠過的暮景,映着玻璃上照出的少女的雙眸,撲朔迷離。
舞蹈藝術研究者島村前後三次前往白雪皚皚的北國山村,與當地的藝伎駒子,以及萍水相逢的少女葉子,陷入愛戀糾葛,簌簌落下的雪掩蓋了一切愛與徒勞……
「愛與徒勞?」
「所以,一切都是虛幻嗎?」
窗外的雪花被風打在窗戶上,基本上都是滴滴塔塔的敲擊聲。
也不知道是不是窗戶漏風亦或者是翻頁的時候掀起的氣流,總是能夠攪動一陣寒風。
似乎在這個時候,雪國這兩個字,讓整個房間的溫度下跌了不少。
也許在被戳破了之後,徒勞兩個字始終貫穿了整本書,也牢牢的鎖死在了大島和也的腦海當中。
那是一種朦朧之美,但是再如何美的東西,始終都是虛幻。
是的,都是徒勞。
這正是這個時候,大島和也才真正的見識到了北島駒的筆力以及他那即為恐怖的構思。
讀完之後,已是深夜。
窗外的雪花早就可以遮住了窗戶的半片格柵,玻璃上似乎有凍結着的冰花,在屋內的燈光下閃着光暈。
大島和也嘆了一口氣,即便是如何揉眉心,始終都無法掙脫開北島駒構建出來的幻境,只好搖着頭苦笑着跟着罵了一句該死的東京人。
頭一次跟着這麼罵自己的。
大島和也苦笑了一下。
和駒說的一樣,真的是徒勞啊。
他嘆了口氣,想了半天,最後還是準備寫點東西出來。
不然,他渾身的雞皮疙瘩根本下不去。
「在東京人島村的眼裏,生命本是徒勞。
趕鳥節不過是孩子們徒勞的嬉戲,就像飛蛾在鋪席上徒勞地掙扎。
駒子寫讀書筆記和日記也是徒勞,每晚奔走於各式各樣的酒席,陪酒、表演更是徒勞,就連她執着的愛情也是美麗的、稍縱即逝的徒勞。一切如病故的行男一樣,終將化為烏有。
島村以旁觀者的視角俯視着雪國的一切,不僅從空間上俯視,也從時間上俯視。
駒子的『摯愛之情不能像一件縐紗一樣,留下實在的痕跡,縱然穿衣用的縐紗在工藝品中算是壽命最短的,但只要保管得當,五十年或更早的縐紗照樣穿在身上不褪色。而人的這種依依之情,卻沒有縐紗壽命長……』
悲觀的島村看到『在駒子身上迸發出的奔放的熱情,覺得格外可憐……』
的確,想到鮮活的生命終將萬劫不復地毀滅,任誰也會悲嘆動容。」
大島和也長長喘了一口氣,他心中有點鬱結,必須寫出來:
但是駒子對待生活,卻是完全不同的姿態。她有着一股明知徒勞偏偏為之的倔強。
「連要洗的衣服也疊得整整齊齊的……」
「不把日常生活安排得妥妥貼貼,是安不下心來的……」
「雖然明知收拾好,還會給弄亂的,但總得去管它,否則放心不下……」
她盡全力追求生命之美,
-
簡介: 一滴血壓塌萬古,一葉草斬碎蒼穹。曾經最為強大的太古禁忌神術太古龍象訣失傳億萬年。無盡歲月後,落魄少年林楓偶得太古第一禁忌神術太古龍象訣。當林楓從世界最北部一個偏遠小城走出之後
-
簡介: 他橫任他橫,我自種我田,若要來惹我,過不了明年。 宅男趙海帶着QQ農場穿越到了異界,附身到了一個落迫的小貴族身上,他的封地是一片種不出東西的黑土地,而最主要的是,他
-
天地間,有萬相。而我李洛,終將成為這萬相之王。繼《斗破蒼穹》《武動乾坤》《大主宰》《元尊》之後,天蠶土豆又一部玄幻力作。...《萬相之王》
-
三萬年前,自稱為「神」的搏天族入侵靈域,百族奮起反抗,最終慘敗,人族率先投誠,百族隨後相繼臣服。 之後萬年,所有種族皆被搏天族奴役,被嚴酷對待,生活在恐怖陰影中。 搏天族征
-
簡介: 【重生+青梅校花+戀愛日常+狗糧+賺錢】身患絕症的陳凡重生2000年,再次見到了自己的白月光校花同桌蘇若初。 前世,兩人的愛情相敬如賓,舉案齊眉,女友卻因為一場車禍意外
-
一個末法時代的鬼巫師車禍被撞死,靈魂穿越,發現自己來了日本,附體在了一個日本人的身上。正想着要在日本闖出一個名堂來,結果順手拿起一份報紙掃了一眼——工藤新一,日本平成年代的福爾摩斯,警察的救世
-
遊戲出現bug,不小心掛機了千萬年,看着無窮無盡的經驗值,任長生只想說,我真的不想升級啊! ……
-
簡介: 少年林軒,靈脈被封,遭人欺辱。偶得://.longtengx.秘小劍,開靈脈,練://.longtengx.功,悟無上劍道,演化攻伐聖術!一劍星辰滅,一劍鬼://.longt
-
簡介: 這個世界上,誰都有可能背叛你,即使是曾經的兄弟。 只為了一棵五百年的雪參,他被兄弟破碎丹田,奪去性命,隨後將他踢下山頭, 誰料神秘雷種進入他心臟,死而復生
-
簡介: 結束,也是一種開始…… 《斗破蒼穹之無上之境》,這是一本斗破續,在這本斗破當中,你們依然會見到繁衍到巔峰的鬥氣,還有着最高級的鬥氣,我們的主角依舊是我們的炎帝,蕭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