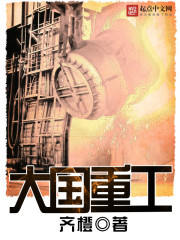絕嫁病公子 005他為她買了新衣
顧九望向屋內月光照射的床榻,她沒打算今日離開,但也不代表要留下來做他的妻子啊?
「怎麼了?」男人問道。
「其他房間沒有床嗎?」
陰寡月笑了笑答道:「只有這間有,一間大堂一間房然後就是廚房沒有了。」
顧九聽着鼻頭有些發酸,站在那裏沒有怎麼動,也不想靠近床榻。體內殘餘的藥力已經漸漸消散了,看來喜茶裏面的藥下得並不重。
擠擠吧,顧九對自己說,她可不想扒一夜的桌子,因為昨日的上吊事件這具身子的脖頸已被勒的僵硬死了,她可不想再遭罪了。
看着毫無生氣的陰寡月,顧九嘆了口氣,都這副死樣子了他還能對她做什麼呢?想着顧九褪了鞋襪,爬上床去。
錦被裏面的花生蓮子還有一些在,顧九伸手摸了幾個放在了榻旁桌子上,又伸手摸了摸,這時一雙冰冷的手抓住她的手,突如其來的冰冷觸感令顧九一顫。
接着一大把花生棗子塞在她手裏,顧九唇角一抽,心道:難為她惹了這麼久,被磕得疼得慌吧。
待顧九重新摸了摸床榻,覺得應該清理完了,頗有些筋疲力竭的躺下。
才聽得身旁男人說道:「是林家的阿嬸替我弄的,她對我很好,我三月參加鄉試時就是她幫我弄得行禮,院子也是她幫我照看着的。」
「鄉試?」顧九偏過頭去,就看到一張近在咫尺的臉,還有宛若幽蘭的馨香,顧九嗅了嗅,嗅到一股脂粉的味道,再要靠近的時候那人已往裏挪了挪身子。
陰寡月望着頭上的紅布簾幔,一顆心狂跳無比,蒼白的臉上又抹上緋色。
顧九有些心虛,她方才確實是想靠近他些,她忙道:「不是在長安嗎?怎麼還要參加鄉試?」
陰寡月笑了笑:「我是庶民要參加了鄉試才能參加會試,只有長安城中的貴族才能直接賜予進士出身。」
「呀,那你九月不是要參加會試了?」顧九按這具身體的記憶里關於科舉的映像說道。
「嗯。」陰寡月微微頷首。
「只有兩個多月了?你能行麼?」顧九問道。
陰寡月心裏一暖問道:「你在關心我麼?」
又像是想到什麼似的,陰寡月摸到她的手一握,道「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顧九想甩開他的手,卻又怕再弄疼他,只好道:「顧九。」
他緊緊地捏着她的手道:「九兒,你等我考取功名再做打算可好?」
「你不是……」顧九正要開口問他,他不是罪臣之子嗎?卻又怕傷了他,只好住嘴了。
許是知道了顧九的意思,陰寡月勾唇道:「我是庶民。」他是獲罪的庶民,所以有權利參加科舉,只是擺不開陰寡月這個名字罷了。
顧九默默頷首,突然襲來的困意將她吞噬,她就這樣靠着他昏昏然睡去。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雖然沒做什麼倒是睡在一張榻上,他們之間的關聯再也剪不斷。
陰寡月伸手替身旁的顧九掩好喜被,這才想到她身上的嫁衣還沒有褪去,這樣睡她不會舒服。
撐着疲憊的身子,寡月輕閉着眼眸,摸索着將顧九身上的嫁衣脫下,只留下一身褻衣,她很瘦,看着只有十三、四歲的樣子,也不知及笄了沒有?這樣脆弱的身子並不適合過早的經歷人事……
月光下他突然睜開眼睛突然很想認定一個事實,他緩緩的伸手半拉開她褻衣的袖子,女子雪白的右臂上一粒守宮砂躍然於目。
陰寡月微微震驚後,微笑着將她的袖子放下,又褪了自己身上的喜服。他猜得沒錯,那人說的也沒有錯……
寡月將顧九額頭的睡發理了理,掩好被子,復安心躺下。
次日,等顧九醒來的時候藥罐子已經坐在一旁的桌子上看書了,他一身素色衣衫,因為還未行冠禮他的髮髻只是隨意散在肩際,他一手執卷,一手執筆。他的手邊還躺着一個碗,似乎是剛剛吃了藥。
顧九望着自己一身褻衣突然意識到情況不對,開口正想問點什麼,卻聽見病秧子溫溫如如的聲音。
「你醒來?砂鍋里有粥先去吃點。」說着又是一陣猛咳。
顧九低頭看着自己手上的守宮砂,又察覺到自己身上沒有任何不適,反到很舒服,不由的笑自己
-
何謂強者?一念可碎星河!何謂弱者?一命如同螻蟻!楚軒天縱奇才,為救父親甘願自廢武魂,斷絕前路!守孝三年,終得九轉神龍訣,煉諸天星辰,踏萬古青天,鑄不朽神體!任你萬般法門,我一劍皆可破之!劍氣縱
-
厭煩了都市的勾心鬥角,北風回到鄉下的老宅。 養幾隻雞,幾隻鴨,想過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 萬萬沒想到命運給北風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自家的古井居然能垂釣到來自各個世界的物品。 釣起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人間百態,萬千神通,不過一山,一寺,一和尚而已。 新書:《兔子必須死》於6月1日開始更新,喜歡黃粱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
-
冶金裝備、礦山裝備、電力裝備、海工裝備……一個泱泱大國,不能沒有自己的重型裝備工業。 國家重大裝備辦處長馮嘯辰穿越到了1980年,看他如何與同代人一道,用汗水和智慧,鑄就大國重工
-
自從章笑可以報銷旅行經費之後…… 他不是在旅行的路上,便是在準備下一個旅行當中。 住過幾十萬一晚的總統級套房、品過金箔裝飾的華美食物、奢靡盡顯。 征服過危機四伏的亞馬遜叢林、遠眺過喜馬拉
-
內容簡介:九皇叔,他們說我丑得驚天動地配不上你。 揍他! 九皇叔,他們說我行為粗魯不懂禮儀還食量驚人。 吃他家大米了嗎? 九皇叔,她們羨慕我妒忌我還想殺
-
作者標籤: 點擊閱讀收藏此書 我要推薦TXT下載 手機閱讀 最新更新章節 第922章華天英,凌雲峰2016-05-21[最近更新]
-
【狩屍VIP訂閱群:472442513普通群:319824291大量逗比,歡迎騷擾咩~】?末日之啟,一次意外的重傷,丁修被注射神秘血清。一覺醒來,獵魔人血脈開始醒覺,他成為人人畏懼的極限尖兵。
-
顧夕的上輩子, 上學機會是別人的,好工作是別人的,好男人也是別人的。 最重要的是,連錢都是別人的。 一想到這個,她死了都能再吐兩口血。 所以她今生的目標就是有怨報怨有仇報仇, 所有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