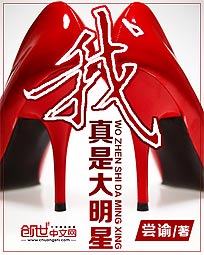花的解剖學 No.30 牡丹燈籠(3)
豐縣縣衙離我們落腳的客棧並不遠,雖然下着雨路上不好走,還是很快就到了。
縣衙是標準制式的建築,跟電視裏演的差不多。外頭有喊冤時可以敲的鼓,裏頭有「明鏡高懸」的牌匾。這會兒晚了沒人,大堂里的殺威棒都靠牆在架子上插着,還有那些寫着「威武」、「肅靜」的標牌,真讓人感覺像拍電影似的。
屍體就停在大堂中央。胡捕頭讓我們在大堂的椅子上湊和先坐了,着人看了茶,自己就急匆匆地往內院去了。過了不多時,胡捕頭引着一個人快步出來。那人見得我們,爽利地揖了一禮。
「在下豐縣縣令葛青松,貴客到訪,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葛青松穿着便裝,看相貌大約三十多歲年紀,毫無我印象中當官的那種腦滿腸肥之態,倒是又挺拔又利落,說話也很乾脆,沒有滿口官腔打哈哈。
見過了這葛縣令與胡捕頭,讓我對豐縣的印象一下子拔高了一個台階。看上去,當地父母官,是些能幹的角色呢!
說起來,豐縣和伊川縣毗鄰,兩縣縣令交往,也是相當必要。聶秋遠站起來,行了禮,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我們,說了幾句客套話。
說話間仵作已經給叫上來了,葛青松揮手示意他們開始驗,自己卻遲疑了一下,說:「聶大人一行的客房,我已着人去準備了。是不是先送二位姑娘回去休息?這裏有死人,畢竟晦氣。」
我溫柔含蓄地立在聶秋遠和駱大春的身後,心裏卻挺着急的。讓我們先回去,不就看不到驗屍結果了?
秋看了看我們,又看了看仵作,忽然說:「那就多謝大人,煩請差人先帶她們下去吧。」
這次他可是一點都不善解人意。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仵作開始脫死屍的衣服了。
畢竟死的是個男人,他讓我們迴避,才是正常的吧。
我和媚蘭施禮告辭。我心裏頭糾結,可又沒有辦法,只好擇機悄悄地呼喚了我的同盟軍:
「夜,你在嗎?發生了什麼事,你要好好地看清楚,回頭,要告訴我啊!」
可是這一回,幽夜公子卻破天荒地失約了。
豐縣縣衙內宅的客房,陳設雖然簡樸,但打掃得很乾淨,住着倒是舒心。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腦子裏全是鬼故事。
三更過了。本來三更是夜出現的時間,可是他並沒有來。我在床上蠕動了半個小時,他還是沒有出現。
他,去哪裏了呢?是沒有聽到我叫他嗎?還是,有什麼別的事情?
心裏頭,有一點莫名的不安。
窗口,有淡淡的亮光一閃。
「夜?」我心裏一喜,翻身下床,推開窗向外看去。
外頭雨已經停了,夜風挾着濕潤的泥土氣息撲面而來,非常清新。
但是我的小心臟卻瞬間凝固了一下,停止了一會兒跳動。
一盞並不明亮的粉色小燈籠,緩緩地,輕飄飄地向我窗子的左首飛去,不一會兒就飄進了花園。
我倒吸一口涼氣。這個,好像是牡丹燈籠呀!
我使勁揉了揉眼睛,但是燈籠已經不見了,而我因為被嚇傻了,也沒看清那燈籠到底是自己飛過去的,還是有人提着。應該是沒有人提着吧?我一時有點不確定了。
可是這牡丹燈籠,應該與案件有關聯呢!
我抓起夜的匕首,揣進懷裏,然後去敲韓媚蘭的門。
不曉得為什麼第一個念頭是去敲她的門。也許因為她是女的,找她比較方便,也許是我感覺那傢伙無論提什麼要求都會漲紅着小臉答應,特別好指使。總而言之我使勁敲了她的門,結果,她!不!在!
深更半夜的,一個女的,幹嘛去了?
然後我不知道應該再去敲誰的門。
我們倆昨晚是提前回來了的,不知道聶秋遠他們的房間是哪一個,而且,我也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對案子的事感興趣。
忽然之間發現,我的心裏頭,對於夜的存在,竟然是如此的依賴。
可是,一條線索……好糾結!而且,主要是,鬼燈籠……這也太嚇人了啊!
我猶豫了二十秒,終於在走廊里叫起來:「哥哥!駱大哥!你們在哪裏?」
沒有人回答我。其實是周圍一片寂靜,靜得嚇人,毫無人類存在的跡象。
-
逆流1979,物質稀缺,文藝即將百花齊放!文學、影視、音樂、娛樂,那種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境界,就在眼前。方言重生在這麼個五彩斑斕的大時代。一隻腳邁進文學,兩隻腳踏進文藝,一步一步,走出一條別
-
四年前,徐東放棄大好前程,為愛挺身而出,嘗盡苦楚。四年後,重獲新生,卻不料未婚妻即將嫁給自己昔日的兄弟。徐東衝冠一怒,誓要問個對錯,沒想到陰差陽錯間,獲得天醫門老祖的傳承。從此,踏上醫道修真之
-
新文案: 大病之後,眠棠兩眼一抹黑,全忘了出嫁後的事情。幸好夫君崔九貌如謫仙,性情溫良,對於病中的她不離不棄,散盡家產替她醫病……眠棠每天在俊帥的夫君的懷裡醒來,總是感慨:她何德何能,竟有此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意外穿越成最後一代人皇,不甘心自己成為聖人的玩偶,讓億萬萬人族成為天庭諸神的傀儡…… 重生的帝辛踏,毅然決然的踏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封神之路! 懟女媧、叱太上、收龍族、定洪荒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穿越香江一九七五。 讓我們一起回顧那些永恆的經典! 創了個群,號:543198555,暗號:1975.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港娛1975》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
-
一心想當明星的張燁穿越到了一個類似地球的新世界。電視台。主持人招聘現場。一個聲音高聲朗誦:「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着烏雲。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暴風雨,暴風雨就
-
「你數理化不及格,大學都難考。看看隔壁小陸,那孩子打小就聰明,他數理化也差,依舊上了北大,說是參加了什麼北培杯保送的,你怎麼不去試試?」「媽,人家顧陸是知名作家,《平面國》《解憂雜貨鋪》《人間
-
邪神祭副本完結可宰白柳在失業後被捲入一個無法停止的直播遊戲中,遊戲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怪物和蘊含殺意的玩家一開始所有人都以為白柳只是個誤入遊戲的普通人後來,他們才明白,是這個遊戲用勝利和桂冕在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