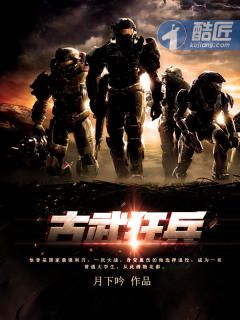長生仙籙 第六十四
刻骨去準備一會兒開店的事,他夜裏招待妖魔,白日招待凡人,真是人魔兩界的錢都賺了。長生想着他真是厲害,一日睡幾個時辰的?她昨夜沒睡都感覺眼皮子有些沉,腦子也沌了堵住了那般。她用力的掐了自己一下,她聽過懸樑刺股保持清醒的故事,但此刻她沒有繩子也沒有錐子,只能是用這種辦法。
姜曲道,「你這是做什麼。」一臉好不心疼的樣子拉過長生的手又給她吹又給她揉,那肌膚勝雪吹彈可破,姜曲又將她的袖子拉上去了一些,低下頭聞了聞,「長生,你是不是抹了什麼?」
司馬鹿鳴捏住姜曲的鼻子,把他的頭推遠了些,臉上是防登徒子的戒備,姜曲道,「長生身上有花香味,你不信自己聞聞。」
司馬鹿鳴拉起長生的手聞了一下,真是有香味,像是荷花的香氣,但又夾雜其他的花香,可他知長生是從不塗胭脂水粉的。長生揉揉眼問,「如果殺了人,可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也只能抵命麼?」
姜曲知她指的是陳槎浩,陳槎浩是值得同情的,連他這七尺男兒聽了那遭遇都忍不住的動了惻隱之心,可動惻隱不表示他認同,「法不容情,律法的作用就是懲戒和警示,是不會管你是不是有苦衷有不得以的,要是人人都說自己不得已去以暴制暴的殺人,那要亂成什麼樣子。」
街上的妖怪散了,樓上姜府的家丁還沒醒,姜曲給了刻骨一錠銀子,當做是把樓上那間房給包了,刻骨收了銀子,在他們快要出了門口時,扔給長生一個火摺子。
長生奇怪扔這給她做什麼,剛想要問,刻骨已經把門關了,很大的動靜迫不及待的關上。是司馬鹿鳴勾住長生領子往後拉,門板才沒拍在她臉上。
姜曲道,「我怎麼覺得他在趕瘟神。」就差沒撒鹽了。
司馬鹿鳴覺得他廢話多,「府尹的府邸在哪?」
……
帝都的官員住的官邸規格大小要按照官階品級,並不是有銀子愛住多大的就能住多大的,屋頂鋪的瓦片不同,大門上刷的漆顏色不同,門的長寬尺度也不同,長生不知府尹這個官職算是大還是算是小。
不過——
姜曲拍了很久門也沒人開,他試着撞了一下門,感覺是裏頭上了木栓,再撞下去怕鬧出大動靜,得翻牆進去抽了木栓門才能推開。長生抓着門環嘗試着「輕輕」推了一下,把那刷着黑漆的木門整扇卸下來了。
這門的質量好像不太好——
他們趁着時候早街上還沒人趕緊溜了進去,長生把門立好,裝作這門還是完好的。她一轉身就看到了王露沾。
她還以為她去了地府了,「王夫人。」
王露沾給他們指路,所謂的護院橫七豎八的躺着,是被藥倒了的。這府尹還真是請了不少人來保護他安全,宅子不大,家丁護院加起來卻有二十多人。
那府尹的腿被陳槎浩刺了兩刀,正從房中爬出來,見了長生大喊救命。陳槎浩舉着刀子走出來,看到他們三人先是一愣,但很快恢復鎮定,眼中殺氣騰騰的問,「你們是一夥的。」
姜曲讓他冷靜,「我們是來勸你不要做傻事,你殺了他倒是解氣了,但你想過麼殺人償命,你殺了他你也要死的。」
「我本來就沒有想過要活。」陳槎浩一腳踩在那府尹的背上,揪住他頭髮扯,府尹不停的求饒還許以金銀珠寶想讓陳槎浩放他一命,陳槎浩道,「像你這等背信棄義之人,你的話我會信麼,留你在世上,只會有更多人冤死妻離子散,留不得。」
那府尹的夫人也是被下了藥,兩腿無力,走兩步就跌走兩步就跌,倒也跌跌爬爬的過來抱住了陳槎浩的腿,「槎浩,他已經有報應了無兒無女,我待你視如己出,不管他做錯什麼,你放他一命好麼。」
陳槎浩把她推開,「我只要他的命。」
司馬鹿鳴踢了塊石頭打掉了陳槎浩手上的刀子,兩人打了起來,那府尹夫人過來扶着府尹要逃。姜曲見陳槎浩被仇遮了眼,說再多估計也聽不進的,他想了想,「長生,犀角呢。」
長生摸出犀角和火摺子,姜曲將犀角點上。
白煙裊裊,異香瀰漫。
陳槎浩並不是司馬鹿鳴的對手,見王露沾現了形,知沒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司馬鹿鳴將他的手反剪在後,摁住他的頭對着王露沾的方向。陳槎浩見到了亡母,人怔住。
第六十四
-
他曾是國家最強利刃,一次大戰,身受重傷的他選擇退役,成為一名普通大學生,從此潛隱花都。 他身懷古武絕學,暴打權貴惡徒,你狂,他比你更狂!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古武狂兵》還不錯
-
你是一名月入2000的小(窮)醫生,飽受生活的壓力和摧殘! 可是,某天一覺醒來,發現自己開了外掛…… 你要做一台闌尾手術,於是開腹探查: 你觸摸盲腸:【盲腸:健康!】 你觸摸結腸:【結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老牌程序員出身的李牧,被命運一腳踹回了2001年高考的當口,他欣喜的拍拍屁股,起身便踏上了一條註定牛X的道路。 重活一回,李牧有他自己的追求,賺錢只是牛X的初級階段,至於登上時代周刊、制霸I
-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當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來襲,陸為民該如何重掌這人生際遇?從畢業分配失意到自信人生的崛起,詭譎起伏的人生,沉浮跌宕的官場,一步一個腳印,抓住每一個機會,大道無形,行
-
李謙重生了。 另外一個時空的1995年。 在這裡,他當然比普通人更容易獲得成功。 但成功是什麼? 錢麼?或者,名氣?地位?榮耀? 都是,但不全是。 有了那回眸的淺淺一笑,那牽手的剎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關於透視邪醫混花都: 窮學生陳軒,無意中獲得絕世邪醫傳承,習得醫道聖手,開啟透視神瞳,從此縱橫花都,恣意風流!各路極品美女紛紛而來,陳軒表示我全都要! ……
-
簡介: 修煉了將近五千年的方羽,還是沒有突破鍊氣期…… 「我真的只有鍊氣期,但你們別惹我!」喜歡本書的讀者記得點擊追書或收藏哦~
-
世事如棋,有人身在局中當棋子,有人手握棋子做玩家。 大玩家擺弄蒼生,小玩家自得富貴。 秦風活過一世再重來,睜開眼,便要從棋子變玩家。 然則大玩家不好當,姑且,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