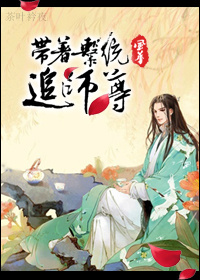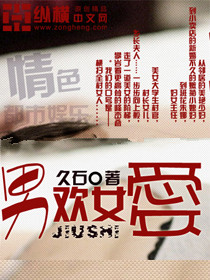墓地挖出的靈異古物 第2章白雀祠的傳說
散發着陳腐氣息的古舊祠堂,在濃重的夜se中綻放出犀利的白光,白天剛剛裝上的千瓦日光燈,光線寒洌,將祠堂陰森大廳里的物件賦上了光明的外衣。/www.yibigЕ.com/正廳靠牆居中的一條黑漆梯形供桌上,高低排列着一排排小巧的牌位。此外,屋子正中擺一張精緻的木桌,桌面上托起一個長約三尺的玻璃柜子,裏面除了一塊紅se墊子別無他物。
唐澤和陳俊踏過高高的門檻,也顧不上和迎上的兩個兄弟招呼,便徑直走到柜子旁邊。
陳俊指了指玻璃櫃,喘着粗氣說:「喏,澤哥,你自己看吧。」說完繼續大口喘氣,他被唐澤拉着一路趕的實在太急了。
唐澤仔細的看着,眉頭緊緊擰起。柜子中果真是空空如也,他下午親自放進去的佛瞳不翼而飛!
而奇怪的是玻璃完好,鎖也完好,除佛瞳不見了之外其他一切都安然無恙,完好如初。
唐澤圍繞柜子轉了幾圈,又把周圍可能的地方都細緻地檢查一番,始終也沒找出半點線索。
「澤哥,我們都找過了,沒有疑點」一個兄弟說道。
「是啊澤哥,剛一停電我們就點燈,前後都不到半分鐘,這…這也太他媽邪乎了!」另一個兄弟接着說,眼中仍存有驚懼的痕跡。
唐澤看了看他們,沒有說話,轉臉又盯向柜子,深深沉思着。
大廳上方的明燈依然放射,將大廳映得一片慘白。玻璃反射出的燈光映在唐澤眼睛裏,分外的刺目,像是一個嘲諷。
「澤哥,你看這會不會是…」陳俊終於氣息平穩,拍了拍唐澤,一邊說話一邊抬眼看向廳上的壁畫,目光意味深長。
唐澤愣一下,視線移了過去。在供桌後面的牆壁上,那幅經歷了數代春秋的僧人壁畫,已然是殘破班駁,僧人的形象也已經變得模糊。唐澤久久望着壁畫,眼神越發的疑惑。他完全明白陳俊講的是什麼,然而…那可能嗎?佛瞳難道真像傳說中的那樣能自己走動?
陳俊似乎是在等着唐澤的回答,可唐澤一直呆着不動。他望着那副壁畫以及眼前一排排先人的牌位,一言不發。他忽然想到那是絲竹鎮兩大家族歷代祖宗的牌位。絲竹鎮共有兩個大姓,一是唐姓,另一個是鐵姓。
相傳唐明皇年間,有兩位名喚唐舉和鐵遠的結義兄弟,在家鄉犯下殺人重罪,背井離鄉,毅然帶上家眷自遙遠的雲南遷至東北的一片荒寂土地。那時的東北也算是個人口繁盛之地,可命運決定唐舉和鐵遠只能遠離喧囂,選擇了一片幾乎為人遺忘的莽林地帶。這地方林木攀延繁盛,位於滄海與石崖之間,多為當地盜賊出沒。二兄弟身懷武功,品性剛蠻,正好派上用場,不久便在血刃中成了莽林群賊的首領,成立了惡鎮四方的龍頭會,從此繁衍生息,才有了今日的絲竹鎮。
換句話說,絲竹鎮人追根求源是盜賊的後裔。所以很長一段年代裏,當地人最大的遺憾和恥辱是他們中間從未有過一位像樣的文人名士出現。
終於在明朝永樂年間,一位雲遊的僧人來到這片莽林地,即刻被那片片連綿蒼茫而不失俊逸的林木吸引,隨口嘆道:有地如此,吾身有棲矣!從此安身莽林,與村民們一起伐林躬耕,早晚清修悟佛,傳經佈道。僧人還擅長音律,閒暇之餘常為村民們演奏蕭笛,韻如天樂的管音使莽林人第一次知道世間竟還有比財物更為美麗的東西,於是爭相效仿,以致於莽林人不久便成了方圓百里內最善蕭笛和最具雅致的群體,絲竹鎮由此得名。
但雅致歸雅致,雅致終是不能消化野蠻,路經絲竹鎮的人們還是會頻繁地遭遇強盜。不同以往的是,這時遭遇的強盜往往會腰裏懸掛個竹蕭或者竹笛,有人甚至還見到左手擎笛,右手握刀,以笛音為號的強盜集體蹦出來行兇,形成當地獨樹一幟的強盜文化。
而無論如何,渴望文人的村民們還是把這位能文善字的高僧奉若神明,集資在莽林東北方位最高處修建了一座簡陋的廟宇供僧人清修,同時也把各自的娃娃們送往寺里求僧人授文傳字,期望着某日這兒能出現個狀元郎,於是寺廟又儼然成了村上學堂。後來那僧人在寺門牌匾上揮毫題就的「文達寺」三字,便是這一期許的體證。
絲竹鎮確實出了狀元,是那高僧首批教導的學生之一,名叫唐元。唐元高中後衣錦還鄉,對文達寺大興土木,之前破落簡陋的文達寺煥然一新,
-
一夜激情,美女竟然是自己的頂頭上司,集團總裁!而且……而且……居然還要和自己結婚!Oh!MyGod!天底下居然還有如此的好事!可是,面對極品美女總裁,於飛...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內容簡介:左手絕世醫術,右手無敵道術。含冤三年的鄉村小子出獄,如虎下山,如龍入海。本想懸壺濟世大展宏圖,卻有各色美女纏上。桃運太強怎麼辦?小神醫也是很無奈啊。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鄉村
-
【文案一】她愛他的一切,但最愛他的手,這雙手抱過她,也揍過她;替她寫過語文作業,改過物理錯題;為她彈過鋼琴,打過架子鼓;帶她飈過車,牽她走過無數路口;更為她戴..
-
又名《港島財閥崛起》、《財閥從港島誕生》 這是一個掌權十五載的財閥二代穿越香港五十年代的故事,男主角不...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金錢玩家》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
-
簡介:   兩世為人,中醫天才變為普通實習生;從此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打臉醫德惡劣的主任,迷倒風華絕代的佳人,再度踏上巔峰之土,成就前世未能
-
穆凌淵前世心狠手辣,死了一次本想洗心革面。哪知道重生還帶贈品,復仇系統一聽就不是什麼好名字。作為君千澤唯一的徒弟,穆凌淵不得不在系統君的壓迫下,走上了一條活雷鋒(萬分拉仇恨)的道路。什麼?君千
-
從鄰居的美艷少婦,到小賣店的新婚不久的嫩菊小媳婦,到班花朱娜,婦女主任,美女大學生村官,村長女兒,鄉長夫人……一步步向上般,走了一道美女的階梯,攀岩着更高聳的..
-
我是他人眼中一無是處的廢物贅婿;但,上門女婿,未必不能翱翔九天!...《最豪贅婿》
-
簡介: 穿越到以武為尊的未來星際,為了避開勾心鬥角,羅碧隱瞞了自己覺醒異能的事。 誰知有人不長眼非要找事,堂妹先是搶她的未婚夫,接着還想搶屬於她的東西。 羅碧一怒之下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