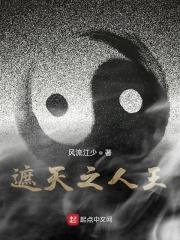三國之風流曹子建 第五十六回 刀斬黃門走狗
天空細雨如牛毛,除了早就被淋透的眾人,曹節溫潤的面頰上也被沾染了一層細細的霧氣,如出水芙蓉一般,眉上卻又帶着一絲難以舒展的憂愁。兩個都是自家兄弟,可車不同軌,夾在中間叫她好生為難,突然之間接受了這個特殊的使命,是出自哪個傀儡天子也好,或說是那個真正坐擁漢家天下的男人也罷,無論如何她也知道,今日之事對於曹丕和曹植來說,將是決定誰更適合一條通往那個未知高度的道路。
曹節不確定這是不是那個即便她這個女兒都看不清的父親給這兩兄弟八年之後再度「相逢」而出的考驗,可曹節卻清清楚楚的明白,從小時候就開始暗暗較勁的兩兄弟從此將再無和解的可能。而最讓曹節疑惑的卻是,那個始終猶如遮了一層面紗的父親是不是真的希望他們和解呢?
而此刻站在曹節身後的黃門侍郎卻是一陣頭大,他現在騎虎難下,其實他倒是不介意再裝一回孫子,像條看門狗一樣搖搖尾巴乖順的退後以求得自己安然無事,可他卻知道自己身後的那一雙眼睛正緊緊的盯着自己,若是這個當口他不去銜接,恐怕以後他也沒有機會在那座雖然姓氏不明,但依然威嚴赫赫的皇宮裏大搖大擺的踱步輕走了。
說到底,黃門侍郎張義府是從心眼裏恨着他那個名不副實的主子的,當初車騎將軍當朝國舅董承和那個大耳皇叔劉備密謀誅殺曹操,一向聰明卻性子懦弱的劉協居然親手寫了血書衣帶詔,等到事情見敗,國舅爺倒算敬業,大不了死了個乾乾淨淨,可恨那大耳賊平日裏滿嘴的匡扶漢室,竟當下就撇下了主子自己逃命去了,到了現在聽說還窮困潦倒談何匡扶社稷?
這些張義府都從不置喙,如此人人自危的亂世,能保住性命就已然不錯,何苦要掙扎着跟當今權柄彪悍的曹大將軍作對呢?可張義府唯一覺得可恨的卻是那個根本沒有絲毫權力的傀儡皇帝,明明已經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卻總夜夜抱着那刻着「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據說藝術性甚高的前朝宰相篆書大字的玉璽痛哭流涕。
張義府總想,誰當那個每天除了可以臥龍床叫人羨慕不已、其餘就是坐在一張還不夠他一個小太監躺下伸展懶腰的皇位上摁印子的皇帝,還不都一樣?做個太監也沒什麼不好,總比想殺人卻被差點反殺,最後落得自己的皇后被誅殺,連個遺腹子都沒留下、一屍兩命的下場要好得多吧?
所以此時此刻,張義府心裏是恨着那個自以為受命於天卻難以永昌的主子的,明明自己君已不君,卻偏偏下了一個叫自己如此為難的命令,雖然張義府也知道這個命令到底是出自誰手,可黃門侍郎說白了也就是一個身殘腦更殘的太監,自己不得痛快,怨恨起人來哪兒還分得清誰好誰壞呢?更何況,這個干戈寥落的世道,哪兒還會有什麼好人,即便真有,估計也是像咱們的國舅爺一樣死無葬身之地才算合適吧。
容不得張義府在心中有過多的時間去捋清現狀,曹植一雙冰冷的眸子早已將他凍了個寒冰三尺,張義府終於咬了咬牙,死就死吧,反正也沒想着能在曹家人手中能活個百八十年的,只求二公子還能記着咱家的好,給家中老母送點自己恐怕來不及去吃的上路飯。
「四公子,典韋身為虎豹營騎督,卻慫恿手下將士意圖謀反,此為叛亂大罪,罪不可恕。更何況,四公子不知,在你離開許都城的這八年,典韋屢屢偏袒賊人,擾亂國家法度,更是在當初對袁紹一戰中,由於他下了將士埋刀埋槍的命令,致使虎豹營和飛熊軍未能完成截擊敵人糧草的使命,如此罪名累累之人,四公子當真要力保到底嗎?」
張義府理清了思路之後,說話又恢復了平日裏滴水不漏,殺人不見血的宦官本質。只是等他再看到曹植手上動作時,還是不由一驚!
聽了張義府對典韋過去一番罪名的整理歸納,曹植只是露出一絲玩味的笑容,同袍短刀雖是後世偽造瑞士軍刀,但比起這個時代的冶煉技術,同袍刀依舊是鋒銳無匹,此刻只見他緩緩走到張義府身邊,刀鋒輕輕划過張義府的小腹,並繼續向下。
曹植嘴角噙着一絲微笑,在張義府耳邊用只能兩個人聽到的聲音道:「侍郎大人,當初那一刀如果不夠斷子絕孫的話,今日曹植倒是可以代勞!」
張義府猛然大驚,同時眼中閃過一絲怨毒之色,誰說宦官無羞恥之心,起碼在每個入宮淨身的太監心中,那決定一生命運的一刀,將會是他一輩子都不能
-
江辰意外被一個叫征戰樂園的存在帶到了遮天世界,親眼目睹了九龍拉棺離開泰山。不好意思,為了葉凡以後不因為交不起停車費而不回地球,這奔馳E200是我的了!這是一個不正經的遮天,另加一個不正經的人王
-
簡介: 【家族修仙】【凡人流】【御獸】 異寶傳說、八荒潰散/> 隱忍家族、驚天秘密 ……… 重生至太行山葉家,身懷萬靈圖鑑 御獸、御山川、御草木
-
簡介: 我若執魔,天地無仙!我若執天,天地無魔! 這是一個起始於雨之仙界的故事,一個『我命如蝶斬輪迴』的世界! 回首凡塵如煙,一笑淡了明月...只為她,橫行雨界!
-
「看來,我也只能把自己煉成一具活傀儡了。」###這是個詭道修仙的異界,名為大幽王朝的國度由嗜血者們統治。道門信奉外神,以祭神儀軌求取仙途長生;深山峻岭之中,有妖魔棲息;荒廟古剎,藏邪靈詭物;狐
-
上古時代,妖族絕跡。近古時代,龍族消失。神道大昌的時代已經如煙,飛劍絕巔的時代終究沉淪……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那埋葬於時間長河裡的歷史真相,誰來聆聽?山河千里寫伏屍,乾坤百年描餓虎。天地至公如
-
陰天域界,妖魔橫行,邪祟叢生。凡人託庇在超凡勢力下苦苦生存,修真宗門高高在上,道君漠然俯瞰螻蟻,而「仙」成為最大禁忌。少年李青雲,侯府庶子出身,天生廢體又遭嫉被陷害,流放道觀,原以為只能青燈長
-
簡介: 【神醫+鄉村都市】傻兒王根撞見小寡婦被欺負,慘遭村霸父子倆追殺,幸得蛇仙娘娘傳承,獲得陰陽蛇瞳,從此開啟一段多姿多彩的幸福人生
-
簡介: 我為天地一仙人,負劍踏山河。道是荒墳老樹狐狸洞,鄉言村語志怪異。 看那老龍出潭澗,猛虎坐山丘。聽我急急如律令,且召神來,又役鬼去。 馮虛御風逍遙遊,群仙宴我飲,放
-
人間萬里,妖邪遍地。人命如草芥,眾生似豬狗。“這個世道該變一變了。”那個少年站在渭水畔,開口笑道:“人間有妖,我有刀。&ld
-
簡介: 凡人流、穩健、冷靜、天道酬勤、殺伐果斷陳易穿越修仙世界,自帶紫金命格:【命貴紫金:天道酬勤,凡所堅持,必有所成。 】有此命格在,哪怕身為宮家最低等的賣身奴,陳易也並未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