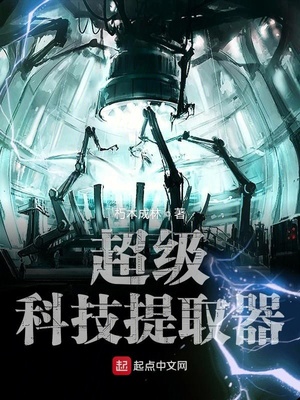被侮辱與被壓迫的 十 第一課〔3〕
找那女人討錢的下一回,日子到了臘月二十二。
我記得清楚清楚,第二天就是小年。
我娘說:「明個兒灶神爺就要上天請財神爺啦!
我還記得,這天一點也不冷,天空陰沉沉,要塌下來的樣子。
黃大麻子也很興奮,牛眼睛炯炯有神,連麻坑都閃射出燦爛的光。
我瞥着他說:「咱們出來七、八趟吧?」
他說:「有那麼多?好玩不?」
我說:「頭兩趟挺有意思,後來就沒勁兒啦。」
他說:「小子兒,爺們不會讓你白跑腿。」
我說:「啥意思,難道你給我發工錢?」
他說:「工錢的肯定沒有,可以弄兩個爆竹聽聽響動。」
我說:「給我買炮竹?真的假的?」
他說:「賞你一掛鋼鞭,純二百響的。」
我雖然很興奮,但想了想說:「放小鞭是小孩子幹的事,我不要。」
他一愣,問:「你想要啥?」
我說:「十個『二踢腳』,砰砰地多響多過癮。」
黃大麻子一聽,立馬沒聲了。我盯着他,只見他轉轉眼珠,猶豫一會兒,最終還是答應了我。當然,他並沒有滿足我的全部要求,在數量上減去一半,同意給我買五個雙響炮。
我說:「五個就五個。」
然後又問:「哪天去買?」
他說:「明天咱就去。」
我們說話之間,又拐進了那條「反修路」胡同里。
其實在此之前,我們也曾來這裏賣了幾趟醬油醋,路過那女人家一、二回,卻沒再見到那女人一面。而且,黃大麻子也沒什麼異常,該打醬油打醬油,該賣醋就賣醋,根本沒有提討錢的事。當事人如此健忘,我這個毫無利益關係的旁觀者,自然而然忘了這回事。
一進巷子頭,黃大麻子就表現出反常的苗頭。
他先藉口我搖銅鈴搖得不響,強行從我手中奪走銅鈴。
我說:「你要幹啥?」
他說:「你搖的不響。」
我說:「還不響?你耳朵聾了?」
他說:「咋能這麼說話?你給你做做示範嘛。」
隨後,黃大麻子表象得也毫不含糊,他把銅鈴舉過頭頂,一邊使勁兒搖晃,一邊扯着嗓子吆喝,那對老牛一般的眼珠也跟着滴溜亂轉,已有點魂不守舍,以至於給人家打醬油、醋時跑了幾回神,倘若不是我及時大喝一聲,他手中滿滿一提兒醬油就倒出了漏斗外面。
「想啥那?」
「都倒外面了!」
我忍不住還吵嚷兩聲。
「看着呢!」
「我看着呢!」
他倒滿不在乎,隨口橫得我。
「都灑了拿啥買二踢腳?」
我一不小心,說出了自己心裏話。
「小子兒放心吧,五個二踢腳一個不會少。」
他竟然笑了一聲,抬手還拍我肩頭一下。
畢竟到了年根兒,家家戶戶都備了不少年貨,買醬油、醋的人不多,沒花多長時間,已經不見有人來買。然而,黃大麻子卻鐵心不走了,他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着煙袋鍋。
我說:「沒人來了,換個地方吧。」
他說:「不急,咱再等等。」
話間,他又劃燃一根火柴,點了第二鍋煙,噝噝有味地抽着。
但是我怏怏不樂,馬上從他身邊拿過銅鈴,叮噹、叮噹晃了起來。
他一見,說:「餓了?吃個麵包墊補墊補。」
和前幾回一樣,他變戲法般拿出一個麵包,遞給我。
有了香噴噴麵包解饞充飢,立馬堵上我的嘴,人也安靜下來。
由此一看,人是經不起誘惑的。
我已經記不得,自己一共吃了多少個麵包。
然而我卻永遠記得,我吃麵包時所衍生出的那種微妙感覺。說得磕磣一點,那就是一種被人豢養的感覺。況且,再加上五個「二踢腳」的特別誘惑,我早忘記了自己姓啥,至於掩埋在心中的「深仇大恨」也已經置之腦後,似乎成了黃大麻子吆喝下的一條小狗。
既然是一條豢養的狗,總有被主人使喚的時候。
這
十 第一課〔3〕
-
【歡樂、虐三、無敵文!】諸葛藍攜【情緒值系統】,在斗羅闖出赫赫惡名!因為他的魂技太抽象,封號來了都跪着哭。百分百被空手接白刃:小癟三給爺跪!聖人之眼:瞪誰誰懷孕,分娩一時辰!憎惡詛咒:打我會竄
-
國術世界,三十年的前第一人,會戰天下豪傑,無敵人間。三十年後,全球武道大會,續寫不敗神話。鎧甲勇士,召喚炎龍鎧甲,橫擊影界,光影大戰,終極一躍。超獸武裝,穿梭平行宇宙,黑與白的交織,沒有絕對的
-
扼殺奇蹟, 一手遮天, 永遠的激情熱血, 不朽的暴君傳說!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機動風暴》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薦哦!
-
方昊,全球最尖端科技公司的掌舵人。從航模到軌道穿梭機,從車模到超智能跑車。從家用產品領域到工業機械領域,從航天航空領域到探索地外行星。星隕科技宣言:「我們專為創造科技而生。」方昊宣言:「我認為
-
自從擁有了能夠把所有東西都人化的能力後,悲風的生活變得一團糟。 遙控器娘,別看着電視上的南孚廣告流口水了,我去給你買。 屎殼郎娘放開我!要是讓你用我的精氣滾球再產卵給我我八個二
-
(不後宮,不套路,不無敵,不系統,不無腦,不爽文,介意者慎入。) 當我以為這只是尋常的一天時,卻發現自己被捉到了終焉之地。 當我以為只需要不斷的參加死亡遊戲就可以逃脫時,卻
-
一個來自異世界的身體與現世的真靈一同出現在斗羅大陸,真正的崛起,存在於生死之間。
-
鬼畜乙女遊戲的官配男主角穿越到現實生活?空有一身霸總的壞毛病,卻沒有霸總的財力和權勢,為了把白狼調教成一個正常人,童心媛唯有忍忍忍……傲嬌千金和霸道少年雞飛狗跳的日常,由此開始! 本站
-
雙男主!洇月絕美!宗旨:究極瑪麗蘇!受超美看到臉讓人一見鍾情那種,吸引變態,雄競,超級寵,受又美又嬌又誘撩洇月是月妖,偶然被系統綁定,去各個位面扮演路人甲炮灰,走劇情。位面一:狗血文的炮灰路人
-
莊周夢蝶,孰夢孰蝶,亦或蝶與我皆為為本真一場重度發熱差點要了梁月的小命,但卻也因禍得福,意外獲得了在兩界之間穿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