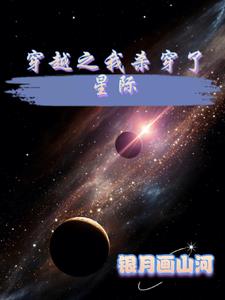昏朝醉暮 第二十一章 幸災樂禍
自打那日在城南救了難產的婦人,朝暮便買了處宅子住在了城南。
那是座挺荒僻的小院子,院前院後都被原來的主人種上時令蔬菜,沿着紅紅綠綠的蔬菜地往前走便可以看到另一處小院子,院裏住着一對老夫妻以及他們年長未娶的兒子。
一開始朝暮並未看到那位老實憨厚的男人,買房的時候只看重了那對熱情的鄰居,後來才曉得那對夫妻是將她當做兒媳婦來看。
拋開老夫妻刻意的撮合不說,朝暮的日子過得還是相當愜意的,唯一不足的是沒有人為她買酒喝了。
扶柳年紀雖小,做派卻跟個老頭子一樣,每逢她打着哈欠懶洋洋地望天的時候,那人就會一本正經地出現在她面前,毫不講情面地潑冷水:「別想着喝酒了,我是不會出去給你買的。」
頓了下,又面無表情地補充道:「也別想着讓大牛哥給你捎帶,我已經告訴他你身體不好不能飲酒。」
朝暮無聲望天,沉默良久終於忍不住掐着他的臉道:「你這人心眼怎麼如此黑?」
或許覺得總被人掐臉影響自己光輝的形象,扶柳特意讓隔壁大牛從集市上捎回來一套烹茶工具,然後擺在朝暮面前,讓人閒着沒事烹茶喝。
朝暮抱着小巧的紫砂壺欲哭無淚,其實她也知道扶柳只是單純地為她的身體着想,可讓一個自由慣了的人守着茶壺烹茶實在有點困難。
自打從北荒歸來,她每日都會重複做那些噩夢,埋藏在胸腔的那顆心臟就會疼得厲害,像是凡世里最殘酷的凌遲刑法,那執刑的劊子手握着鈍刀一片一片地割她身上的肉。
除了疼,還是疼,一開始她受不住,每次都在極度恐懼中尖叫着醒來,後來似乎是麻木了,盯着滿頭大汗睜開眼睛呆滯地望着深邃的夜色。
許是被她日漸麻木的情緒感染,小小年紀的扶柳變得越來越老成,不許她傷春悲秋,不許她過度飲酒,甚至連睡覺都要看着她閉上眼睛。
有時候她會突然生出一種扶柳才是轉了世的柯醉的錯覺,可是她心中很清楚,扶柳不是柯醉,真正的柯醉不會回來了。
即使再沒有在柯醉投生的那戶人家面前露過臉,她還是時常躲在暗處偷看那個小小的人。比如那位夫人果然為他取了柯醉的名字,比如他何時長出了一顆乳牙,比如他何時學會了走路,比如他何時學會了說話……
有時候坐在窗前望着那張秀氣的小臉,她會覺得自己很悲哀,就像是一隻離了隊的大雁固執地沿着自己心中的路線飛行,即使猜出來是錯的,還要頭也不回地走下去。
第一次出現在柯醉面前是在他六歲的時候,那日他穿了件短短的青布袍子,面前擺着個灰撲撲的破舊書包,學堂里教書先生在抑揚頓挫地念書,他卻心不在焉地四處張望。
然後他們的眼神就在春日的空氣中不期而遇,這是第一次她覺得男孩與柯醉很像,他們有着一樣漂亮的桃花眼,每當臉上有情緒波動時,那雙眼睛尾稍就會微微上挑,像是變成一個一個小鈎子,輕易地就將人的情緒鈎進他的眼底。
她就坐在學堂前的台階上等他下學,窗前新生的梧桐樹葉被風吹得呼呼作響,夫子斥責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傳進耳朵。她托着下巴呆呆地想着柯醉的模樣,總是面帶春風的人物被夫子單獨留下來耳提面命,光想着就覺得滑稽。
可是後來望着他單薄又落寞的背影,她還是心軟了,所以為少年出了個餿主意,同時又帶着私心特意提出了桃花酒。
離開私塾後她心裏裝的全是桃花酒的滋味,一路走一路痴想,最後乾脆跑到京城酒館了買了壇酒。
腳步聲響起時朝暮正抱着那壇味道寡淡的高粱酒往嘴裏倒,本以為是出去玩耍的扶柳歸來,她慌裏慌張地將酒罈往桌子後面藏,結果回頭一看竟看到勐澤略帶疑惑的側臉。
前一刻還慌亂的情緒登時冷靜下來,慵懶的眼神也被刻意的疏離取代,朝暮從凳子上站起來,被酒水泡得格外紅潤的唇瓣沾染上了金色的陽光,落在眼中讓人忍不住晃神。
「你來做什麼?」
充滿防備的語氣,朝暮此時就像一隻被人驚擾的貓,弓着身子做出反撲的姿勢。
勐澤眉毛一揚,眼睛漫不經心地從朝暮身上掃過,背在身後的那隻手伸出來,露出一個不大不小的白色瓷瓶。
「特意從王母那
第二十一章 幸災樂禍
-
避雷!一些世界有點慢,一些又很快無厘頭,謹慎觀看。避雷!有的世界男主不潔、非1v1、專業知識少等等避雷!每個故事主打一個心想事成,沒啥大的波瀾。避雷!前兩個單元有點無聊哈第一卷和第一個世界的第
-
新作品出爐,歡迎大家前往番茄小說閱讀我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你們的關注是我寫作的動力,我會努力講好每個故事!...《麗麗動人不知處》
-
被天降巨石砸回70年代,穿成擁有一堆奇葩親戚的小孤女麼破?夏穎瑩表示不慌,她有自動補貨的自助餐廳在手!即使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匱乏年代,她也照樣能吃香喝辣,混得風生水起!看到夏穎瑩從山裡逮了一隻又
-
七歲的傅雲頂在風雨雷電交加的夜晚苦苦哀求母親救救父親,可母親嫌棄傅明憲的碌碌無為,甩手離開,留下傅雲頂一隻紅色高跟鞋,勾搭起雲城首富秦富,並為他生下私生子,並迫使秦富離婚,當上了首富太太。十五
-
季清霖為了完成奶奶的心愿,與一個素不相識,同樣為了完成爺爺心愿的男人結婚了,殊不知這個男人乃是江北第一豪門顧家的掌權人。他們婚前簽下協議,待一年後便以感情不和為由離婚。於是領完證後,兩人就各奔
-
1V1雙強江清淼vs夜墨殤從小堅信科學的江清淼在18歲時發現自己生活了18年的世界居然是假的,世界觀被打破重組,還被一個自稱螣蛇的人送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面對未知的未來,這個剛成年的小姑娘將會
-
天道向任務者提出了一個請求。正值主神任務者改革期間,這個天道對他說。-我有個孩子,麻煩你替我帶走。所以他綁定了他的第一個宿主,小東西冷清又難伺候,但她很聽話,被天道單獨拉出來的孩子,當仁不讓的
-
作為新人作者,我深知自己的作品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我懷着滿腔的熱情和對文學的熱愛,傾注心血於每一個字句。您的每一次閱讀、每一條建議都是我前進的動力。在這個創作旅程中,我期待與您共同成長,用
-
禁慾高冷的男主VS膽小如鼠人菜癮大愛吃瓜女主,頂着間諜的帽子苟着生活,原本醫學界精英書穿到七零年代的炮灰間諜身上,占了女主位置,女主變女配,生活抓馬,一路吃瓜。...《穿越七零,老公要親親》
-
她,是華國蘇氏集團千金小姐,被眾人唾棄,都說她是病弱千金,是草包,她本不在乎這些打算繼續擺爛,可沒想到,讓家人擔心不已,於是,她不裝了,開始打臉眾人,黑客大佬、音樂教授是她,連國際知名畫師,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