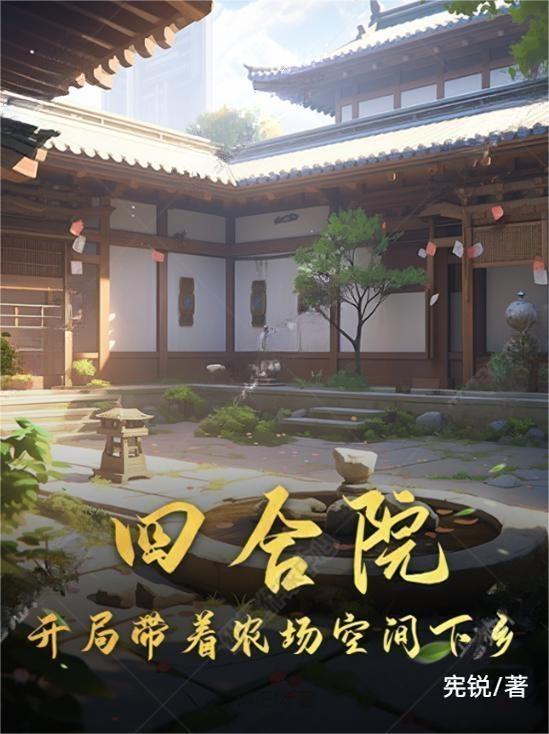風雨大宋 第79章 有進有出
看着周邊熙熙攘攘的人群,全都是鐵監那邊過來的,人人紅光滿面,權二郎飲了一杯酒,把杯子重重拍在桌子上,恨恨地道:「我怎麼如此命蹇!一樣是拉縴的,一樣到京西營田,怎麼我就被派去耕地種田,不進鐵監里!看看你們,一來就有新房子住,錢糧發着,還有假期玩樂,哪裏敢想這種好日子!若是有這種好日子,我也要待下去,何苦不明不白地離開!」
坐在對面的耿新道:「二郎,你也不要只看到好的。我們這日子是好,可要求也嚴,做活的時候不能稍有差池。一出錯,輕則訓斥,重則罰錢,還有可能被趕出去呢。」
權二郎不以為然地道:「這是常事,有什麼!我們以往拉縴的時候,還不是一樣!為了哪個出力哪個不出力,天天爭吵,又有什麼!」
柴孚道:「怎麼能夠一樣?那個進候,縴繩向身上一套,只要出力就好了。現在處處規矩,進了做事的地方,從哪裏走,哪裏能碰哪裏不能碰,什麼都不能做錯。我們做事的人,每日裏還要學着認字。學的比別人慢了,地位錢糧可就被別人比下去了。你的性子,更加待不下來。」
權二郎一怔:「出力做事,還要學着認字?鐵監怎麼會做如此無理的事情?」
耿新嘆了口氣:「豈止只是認字,什麼都要學。我們到鐵監半個月了,初時是每日一個時辰學着認字,三日一考,五日一較,好與不好全部記下來。最近這幾日,聽說爐子要建起來,又要學別的東西。你是填煤燒火的,就要學怎麼填煤燒火——」
聽了這話,權二郎「嗤」地一聲笑:「好笑,燒火要學什麼!」
柴孚道:「燒火不要學嗎?你要學來的是什麼煤,一次填多少,大杴煤堆里一出來,就能估出來多少斤。還要看爐里火色,知道火旺不旺,什麼時候再添。跟你說填煤燒火,是說最容易的事,其他的事要學的就更加多了。鐵監里做事,力氣出的是不如以前多,可要用這兒!」
說到這裏,柴孚指了指自己的腦袋。
權二郎怔了一下,他想不出柴孚說的那些跟燒火有什麼關係,一時說不出話來。
耿新又道:「從學識字,到學如何做事,事事都要考較,如果不過關,便有許多難處。鐵監里做事的人,是分等級的。進來了才知道,我們這些初來沒有通過一次考較的,只是試用,叫什麼借名。只有過了識字關,過了自己做的那一行當的考試,才算真的有了飯碗,叫做正名。」
權二郎好奇心起,問道:「有什麼區別?」
「區別可大了!只有正名,才能真正有資格做事,借名的只能打下手。發的錢糧,正名的比借名的高一級不說,還有各種賞賜,日常補貼,借名全都沒有資格。這可差得多了!」
這其實就是實習工制度,經過了培訓,才能真正上崗。鐵監的待遇定得這麼高,不可能調來了就享受到。所有的縴夫,只有通過了考核,才能算鐵監的正式員工,不然就只是臨時工。工資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能享受鐵監的待遇,也沒有升遷的機會。轉正倒也容易,積極學習,過了考試就行。
耿新和柴孚是權二郎以前在廂軍里認識的朋友,他們命好,被分到了鐵監。這些日子,鐵監里好吃好喝,生活條件讓來的縴夫欣喜不已。但惱人的是,除了每日裏給後來的人建造房舍,修建冶爐,還要每天裏學習。學還不算,經常考試,不斷地把人分流。有那些腦子好的,很快就學會了認字,再去學具體的行業知識,等級噌噌地升了上去。半個月時間,士卒中就有頂尖的,拿到了別人兩倍的錢糧。伴隨着這個過程,廂軍原來的組織形式被打亂,都以下已經完全被派來的吏人掌握。
耿新和柴孚兩人,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屬於中等。兩人都認了些字,現在正學習將來做的工作的專業知識。柴孚圖簡單,選了個燒焦炭的工種,主要是填煤,每天分辨煤種、觀察火焰,弄得頭大如斗。耿新則是澆鑄鋼錠,學的就更加多了。
見兩人煩惱,權二郎道:「你們不必心焦,學的慢一些又有什麼,鐵監又不會開革你們。」
「你怎麼知道不開革?」耿新連連搖頭。「如果只是學得慢,確實沒什麼,無非是少領錢糧,沒什麼前途而已。但若是經常犯錯,特別是散漫不聽使喚的,則就不一樣了。特別是喜歡鬧事的,比如聚眾賭錢,訛人
-
一覺醒來,薛成遠就像是穿越了一個七十多年代的四合院裡,還有隨身的農場空間。賈張氏想要自己的房產,給他們一個小小的教訓,然後,他就會去鄉下。去鄉下也就罷了,還跑到長白山去當一名森林守護者,那可是
-
地球人明曦穿越星際,來到一個以御獸為主的璀璨文明。身份是負債纍纍還得一天兼職三份工養家的苦逼初中女生。人幹事?這是她一個未成年該承受的嗎?雖然人生如此苦逼,明曦依然甘之如飴。因為寵獸是真的香!
-
被他人占據身體的何雨柱,一睜開眼就看到有人偷東西,這個人很是熟悉,偷東西很是熟練,幾乎到了自己家一樣。他想阻止卻發現身體動態不了,小偷離開之後,一個女人進來屋子,以為是溫暖沒想到她說:「柱子,
-
簡介: 本文日更九千。 專欄有快穿系列完結文若干,同步連載文《炮灰姐姐的人生(快穿)》專欄可見~ 冤死後的楚雲梨幫助各種炮灰消散怨氣,滿足心愿 1,剖腹取子(已完結
-
簡介: 古佛被羊頭人身的怪物竊取了頭顱,異鬼在佛殿裡埋下一隻眼睛,從此世間的火熄滅了,黑暗將大陸籠罩。 為了對抗異鬼的入侵,天地間,誕生了日夜遊神。這是說書人世世代代口述的戲文
-
簡介: 蔣寶緹十幾歲的時候被送出國,家裡不聞不問 臨回國前卻被告知,親爹給她找了個聯姻對象 她一氣之下拉黑了父親所有的聯繫方式,決定靠自己 一場慈善拍賣會,她成功拿
-
林陽重生了,回到了1978年的小山村,那個民營經濟即將起飛的年代。前世的他被知青老婆欺騙,拋棄父母進了城,還為堂弟林奇養了40年兒子。重活一世,林陽只想守在父母身邊!順便,他準備趕上時代的風口
-
都說這個圈兒里水深火熱。林楠也想進去看看,林子有多大,水有多深。沒想到才剛進來,就被套牢了……...《那年華娛》
-
南加州大學導演系畢業的李牧,處女作便獲2023年奧斯卡提名。還沒來得及享受這名利場的蝕骨銷魂,便重生回到2002年。這一年《英雄》還未上映,華娛大片時代還未降臨……...《華娛從北電2002開
-
一款名為《詭異紀元》的虛擬網遊降臨現實,世界頓時大亂,各地淪陷為詭異地區。每個人扮演不同的身份,攻略遊戲,獲得百花齊放的規則特性。根據專屬天賦,不同的職業路線,制定攻略路線。玩家每月抽取專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