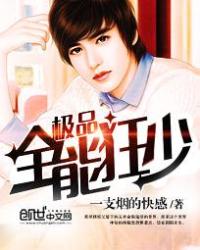三七堂病案簿 四更時 · 五
c_t 她的懷抱同當初在涇南山上的一模一樣,堅實牢靠,帶一點兒母親般的溫柔與穩重。筆硯閣 www.biyange。com 更多好看小說
可就是這麼一個不帶任何旖旎意味的懷抱,偏生令他腦子裏又響起她先前所唱的那段俗曲……漫展青衿疊榻,枕邊零落釵環……然而姓馮的只是單純地把他抱回了屋裏,放到炕上,提着那個包袱便出門去了。趙郎中翻身趴在窗口,望着她只輕輕一跳便躍上房頂的背影,忽而有些淡淡的失望,且懊惱而灰心。
她就這麼走了。
瞧瞧你折騰得多難看啊,人家對你壓根兒就沒那個意思,再折騰又有什麼用處。
酒這東西最奇怪,越愁的時候越上頭。因為自身對麻藥的耐性很高,其實趙寒涇的酒量還不錯,別說這幾杯甜淡的梅酒,便是再飲上一壇燒鍋也省得。但他卻覺得很乏,腦袋像是宿醉過後的那種悶痛,五臟六腑都好似被酒水涮過一遍,渾身提不起勁兒來,只想闔上眼好生睡上一覺。
半夢半醒間,他軟綿綿地被人扶起來,塞進被子裏;那人一邊挪動他,一邊還埋怨道:「怎麼趴在窗台上睡着了,也不蓋被子,也不關窗,萬一着涼了可怎麼辦。」
是馮阿嫣。
趙郎中迷糊歸迷糊,可還窩着火賭着氣,只把手去推她肩膀,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你找你那個酸秀才去,還管我作甚。」
「什麼酸秀才苦秀才的,做的什麼夢。」馮阿嫣失笑,她只當他醉了說夢話,欺他正酣着聽不真亮,清醒後也未必會記得,於是站在炕邊,俯過身,偷偷地伸手去描他一對眉毛,小聲地嘆着氣,「我呀,我眼裏可只你這麼個甜郎中。可你這郎中呢,倒忒不教人省心了,饒是我有意想做個柳下惠,也快架不住你一天三遍地蹦躂。」
她作怪的那隻手忽而被捉住,小郎中的嗓音清清冷冷地響起來:「做不得柳下惠,那我便請你當個登徒子,如何?」
萬萬沒想到,被人逮了個正着,馮阿嫣見他目光明淨,心知自己方才那番話全被小趙郎中給聽了去,難得慚愧了一回,竟不知該如何作答。賀先生所託之事,她至今還捂着沒跟趙寒涇講過,倘若現在正正經經地與趙郎中剖白,勢必要把兩年前、甚至於更久遠的過往給牽扯出來,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一來呢,她不是馮煙那二愣子,以為拿着個信物便能充作父母之命、便能高高興興把人給抬回家;二來呢,自己同趙寒涇的相遇過於巧合,巧合得就跟有人安排他倆相親似的。當初她不信趙郎中,無端生出許多事來;同理論之,如今趙郎中也未必會信她,沒準兒還要跟她追究當初馮煙暴力「驗貨」給他遭的委屈。
倘若自己繼續扮出副嬉皮笑臉的模樣,再講幾句調笑話,輕輕地把這茬兒給揭過去呢?
那她可真就純屬混蛋了。
趙郎中見她不答話,半坐起身來,借着酒勁兒冷笑:「怎麼着,方才還誇我甜來着,這會兒便下不去手了是麼?」說着便扯定她那隻手,攥得死死的,胡亂往自己衣襟兒裏頭摁。
「!」觸及一片溫熱的胸膛,馮阿嫣驚了一跳,下意識把手往外抽,但趙寒涇就是不撒開。即便是小郎中使出了吃奶的勁兒,對她而言也不過爾爾,但她唯恐硬拽會傷到對方的手指,心想不能和酒懵子計較,不得不咬着牙耐下性子,試圖先跟他講道理,「你知道你這是在幹嗎麼。」
她問,你知道你這是在幹嗎麼。
他心想,知道啊,怎麼能不知道。
「吃酒歸吃酒,難受歸難受,我人可還明白着呢。」其實趙郎中這會兒也反應過來,自己一時衝動都幹了些啥,但他仗着自己肚子裏那二兩酒、仗着這兩年來姓馮的再沒有傷到他過,鐵了心不肯收場,卻連呼吸間都帶上壓抑不住的顫抖,「甭跟我打岔,我只問一句,你到底把我當成什麼?」
問完他便後悔了。
怨不得姓馮的,是他自己把自己給逼上絕路的。萬一人家說,我只把你當兄弟、當同夥,就是不肯跟他談男女之間那點兒情愛,他除了「哦」一聲,把人推開,把今天這檔子破事兒咽進肚子裏讓它爛死,現在開始戒斷一切曖昧的舉動、跟她保持距離,他還能再做什麼。
真難看啊,趙寒涇,你瞧瞧你都把路給堵死了,真難看。
到頭來他們之間只剩下四百七
四更時 · 五
-
你見過殺雞爆出神級血脈的沒有?你見過殺蛤蟆爆出神品武技的沒有?你見過整個世界的女人為他一個人男人瘋狂的沒有?肩扛屠龍刀,手握諸神劍,哥就問一句,「媽的,還有誰?」宅男龍飛帶着一款狂暴系統穿越而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超級兵王蘇辰,卸甲歸田重回都市,掀起八方風雲!曾經揚名世界的兵王,讓所有人為之折服! ...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超級兵王混都市》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為了男人的承諾,蕭晨強勢回歸,化身美女總裁的貼身保鏢,橫掃八方之敵,譜寫王者傳奇!他——登巔峰,掌生死,縱橫世界,醒掌天下權;泡美女,擴後宮,玩美無數,醉臥美人膝!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
-
會點小武功,懂點小醫術,有點不要臉,少年秋羽來到大都市充當校花保鏢,當寂寞的世界出現清純小蘿莉,嬌蠻警花,白領麗人,嫵媚大明星等諸多美女,不斷的擦出火花,曖昧叢生,他能否守身如玉,繼續純潔……
-
入贅三年,所有人都以為可以騎在我頭上。 而我,只等她牽起我的手,便可以給她整個世界。
-
「我們結婚吧!」當這一句話從美女總裁口裡說出,李塵只感覺頭暈目眩!「美女,哥賣藝不賣身,想要我的身,你要給錢!」這是一個絕美總裁倒追的故事,想要得到我的心,先要得到我的身!兵王失身的故事就此開
-
家族棄子周辰重回都市,立誓拿回自己的一切,踩紈絝,收徒弟,攬美人;偶得邪神魔血,為活命,修法術、悟天道,踏上逆天改命之路。
-
陸逸,一個身懷醫術的超級高手,為尋找未婚妻,來到繁華都市。他腳踩敵人,懷抱美女,一步步走上人生巔峰……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絕品神醫》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