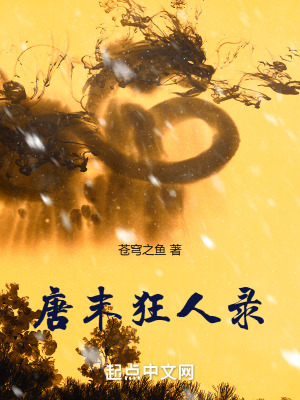大明元輔 第281章 朝歸倭附(十五)端水
,!
高務實認為,有明一代的皇權根本沒有到達所謂「獨c」、「空前膨脹」的地步,這一點除了國事決策的過程可以證實,也可以從大明言官——尤其是原歷史上萬曆中後期他們對皇帝的個人批評,甚至應該說猛烈抨擊可以證實。
其實早在明代以前,中國很多朝代都設有專門的進諫官職乃至相關部門,負責勸諫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無道而損害整個統治階級,乃至國家整體利益。
這就是文人所謂的「道」,也是儒家學說中高於一切,當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於君主的最終原則,更有意思的是,他們認為這也是「忠」的最高體現。
所謂犯顏直諫,便是建基在這個「道」之上,這也真正解釋了為何敢於直諫者往往為後世冠以「忠臣」之名。
當然,諫官固然有責任勸諫乃至批評君主,但無論是何朝何代,言官進諫都不是為所欲為的,而是有着許多語禁與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倫在《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中說:「這些戒律(言官進諫時需注意的語禁以及各種限制)包括不得揚君父之惡,嚴禁以下訕上;臣子進諫要『不可則止』,即在規諫君主時,君主如不採納,必須適可而止;『非禮勿言』,即臣下進諫時必須注意事理、形式、態度、分寸,恪守禮法,講求進諫的態度和技巧等等。
與這類觀念上的戒律相應,歷代法律都有懲處言罪之條,如非議朝政、觸犯忌諱、妖言惑眾、冒犯君長、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這項各代王朝皆為言官群體遵守的規定,到了明代,尤其是歷史上的萬曆中後期,偏偏卻遭到了嚴重的衝擊。
言官對於萬曆批評之激烈,甚至可以說是對萬曆個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擊。這種激烈,恐怕是整個中國歷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評》中,對言官批評萬曆情況有這樣的描述:「早在萬曆十七年,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毒俱全;
萬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張養蒙也指責神宗『好逸』、『好疑』、『好勝』、『好貨』。這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幾乎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將神宗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之中。」
又如《明史》記載,戶部給事中田大益在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上書抨擊萬曆個人操守:「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異皇陵為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為創業之祖而災,長陵為奠鼎之祖而亦災
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為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
如夏桀隕於瑤台,商紂焚於寶玉,幽、厲啟戎於榮夷,桓、靈絕統於私鬻,德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
在將萬曆比為桀、紂、幽王、厲王、桓帝、靈帝、徽宗等歷史著名昏君後,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說道:「覆轍相仍,昭然可鑑。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託身於天下哉!」
這罵得可夠狠?說是狗血淋頭也不為過了吧?可是朱翊鈞對此的態度又如何呢?
面對如此鋪天蓋地的批評,甚至是對於皇帝個人的全方位攻擊,萬曆對此的態度居然只是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理會。
對此,《明史·田大益傳》是這麼記載的:「上章者雖千萬言,(萬曆)大率屏置勿閱。」——任你罵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當沒看見。
朱翊鈞這樣的反應只是因為脾氣好嗎?顯然不是,他要是脾氣好,當年張居正怎麼差點被挖墳鞭屍的?
原歷史上萬曆對待言官的集體激烈抨擊乃至謾罵,皆采以留中不發、不予理會的方式冷處理,其實是從側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後期皇權的疲弱,根本到不了所謂「君權空前絕後的膨脹」。
而這些,也正是之前所提及「尤其如萬曆等怠政之君主權力,始終無法恢復於洪武永樂朝之皇權巔峰之因」。
然而在後世很多人那裏,每每論及言官之直言,便常有論者便要提出所謂「廷杖之下,臣子噤若寒蟬,不敢奏對忤旨,甚至只懂阿諛奉承如此便造就
第281章 朝歸倭附(十五)端水
-
暫無介紹
-
暫無介紹
-
暫無介紹
-
暫無介紹
-
暫無介紹
-
暫無介紹
-
暫無介紹
-
暫無介紹
-
暫無介紹
-
暫無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