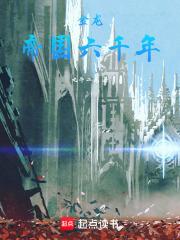我的1979 874、孤家寡人
更新:09-08 00:13 作者:爭斤論兩花花帽 分類:玄幻小說
李怡這一次很聽話
辛虧回去看一趟
他連番感嘆自己的先見之明
她也是解放後隨軍從東北過來的
你們是不知道
我兒子在呢
豁牙老太太道
何老太太不屑的道
一個打着髮蠟的老太太
納鞋底的婦女道
怎麼能說燒就燒
怎麼都不成的
看着盛怒而去的老太太
何芳要去冀北
李和道
-
簡介: 好消息:穿越到夢寐以求的二次元世界了。壞消息:穿越的是火影世界,還是沒有血繼限界的平民孤兒,跟鳴佐同屆。 就在柳生準備當一個小配角,爭取活過木葉崩潰計劃、六道佩恩襲擊木
-
簡介: 路明非:前世我是一名追逐偉大的魔法師,卻被詭計多端的奸人(神)所害,眷屬背叛我,手下驅逐我,甚至整個世界都隨之崩塌。 重活一世,我要向重啟召喚計劃,向更勁更強的邪神貸款
-
簡介: 能穿越位面確實是很好,但是這自動戰鬥就有點太坑了。 「你們不要過來啊,我是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啊!」一邊這樣喊着,一邊林頓錘爆了各路大神,踏上了通向巔峰之路。
-
簡介: 我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不是一個好相處的隊友,甚至我壓根算不上是一個好人。 然而,這個世界上誰也不能否認我是最偉大的籃球運動員,連神也不能!
-
【新書《LOL:我真不是演員》已發,觀眾老爺們請多多支持!】峽谷高分路人王陳昊重生回到S7賽季,以20歲高齡新人的身份坐上蛇隊首發中單位置。在生涯首場比賽遭遇一年後的世界冠軍IG,對線肉雞,五
-
簡介: 作為留守雛龍的諾亞不明白,喜歡為後代挑選養父母的金龍,居然敢對外宣稱他們總是精心照顧與指導後代。 最糟糕的是,他的養父母只是區區伯爵,奈何作為雛龍,諾亞沒得選,只能整日
-
【傳統玄幻+劍道+非後宮+無系統】世間有一樓,名為煙雨樓,煙雨樓樓主李慶之,有着絕代天驕之稱,黑夜之下,執掌生死,然而,天下不知,李慶之身後,還有一人,方才是煙雨樓真正的創始人,掌控天下財富,
-
簡介: 諾頓·薩格一直以來就有個夢想,那就是當個地主富豪,有個大地盤,讓很多人靠着他吃飯,再請幾個秘書,雇一群小弟,有事作威作福,無事看舞聽曲... 憑藉着穿越帶來的『北斗神拳
-
簡介: 這是帝國君臨銀河的第四萬個年頭,大遠征的輝煌早已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中,蘇羽穿越而來,睜開眼看着面前已成廢墟的星球,一臉懵逼。 在這顆星球上,有綿延可達上千公里,已然殘破到
-
簡介: 「給他準備個嘔吐袋,第一次駕駛機娘的契約者,一般都會吐……等等,他怎麼把機娘開吐了?」這是個機娘能幻化成賽車的世界。 機娘是來自異世界的神秘物種,外表如同人類女孩,卻能